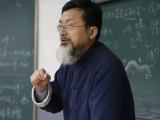
【张泰苏】父亲张祥龙先生和我
三年丧期之后,逢年过节时,我想我会举杯遥祝,祝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在我感知不到的某个维度里遇到另一种更加真实的“林间空地”。我相信他一定能听到,也相信他一定会的。

【陈赟】“原史”: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原初符号形式
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知识谱系,是以原史为原初符号形式,经、子、史等都是从中分化出来的。以原史作为原初符号形式的中国古典思想与以神话作为原初符号形式的古希腊、希伯来思想的一个重大的文明论差异在于,在中国传统中,历史意识与宇宙秩序可以相容,而在后者,宇宙论秩序的经验则着力泯除历史意识。

【范忠信】传统血缘社会组织自治的财团法人运作模式——北宋“范氏义庄”之契约性意义···
以“义田”或家族基金式财团法人为自治经济基础,以五服内宗亲为自治团体成员,以祀祖聚族、扶贫济困、奖学励志为自治公益的目标,这一组织成功地弥补了国家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严重不足。范氏义庄符合今日民法学上的社团、财团两种法人定义,它是中华民族在契约文明、自治文明方面为人类共同价值所作贡献的典型样本之一。

【曾海军】恻隐之痛:一种由近及远的普遍性
由恻隐之痛阐明的一种由近及远的普遍性,实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巨大的优势,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而看轻了。新冠疫情还未远去,经此一“疫”,人与人之间因病而痛的相互关怀变得如此重大,中国人面对疫情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量与坚定的抗疫决心,离不开传统儒家由恻隐之痛所奠定由近及远这一秩序观念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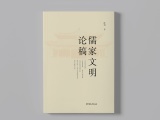
陈明著《儒家文明论稿》出版暨序跋
如果说当下中国的儒学研究,已经进入由哲学范式经思想史范式向文明论范式转换的阶段,本书正是对儒家文明相关问题的讨论。在文化自信、文明自觉以及民族复兴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时候,思考儒学与文明的关系,在这一前提下重思儒教个体论述的可能与必要,是本书的突出贡献。

【张德嘉】和祥龙在一起的岁月
他对我说过:“我感恩美国,感恩他们对我和泰苏一家的慷慨接纳和帮助,基督教文化的合理存在这我也知道,但是,这个世界对东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忽视和不公正需要被纠正,中国文化需要在世界上占据它应有的地位。”

【刘悦笛】美国超验主义与儒家世界观——孔孟与爱默生的深层对话与介入重构
美国超验主义者爱默生被称为“美国的孔子”,深受孔子与孟子思想的影响,但是并不能由此反推儒家也是超验主义,那种把儒家的超越意识视为神秘主义的取向是不正确的。美国超验主义与儒家毕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同一;第二,回归本善的人类本性;第三,追求道德完美主义;第四,重视美的实现。

【喻中】依理治国:朱熹建构的法理命题
朱熹对中国传统法理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依理治国”命题的建构。一方面,理是实现国家治理所依据的最高规范与终极规范。另一方面,在依理治国的实践中,理凝聚并转化成为“德礼”与“政刑”两个层次的规范。在“德礼”与“政刑”之间,“德礼”作为理的直接转化形式,构成了国家治理所依据的基本规范。“政刑”作为理的间接转化形式,同时也作为“德···

【曾亦】《春秋》为“刑书”——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问题
关于孔子《春秋》的性质,古人或以为“经”,或视作“史”。本文立足于汉人视《春秋》为“刑书”的立场,重新审视《春秋》作为“经”的性质。文章认为,《春秋》所以成为“刑书”,实在于孔子曾有得君行道乃至得国自王的本志,而《春秋》不过是孔子用以治世之书,即作为“一王之法”而已。后儒深讳斯旨,遂抑孔子为“素王”,以为孔子不过假《春秋》···

【孙磊】《春秋》“大一统”与国家秩序建构——以西汉国家治理为中心
一方面,“大一统”学说塑造了西汉国家秩序的神圣根基,董仲舒提出孔子作春秋,王者受命于天和阴阳灾异说,接续传承古典“天道宪法”,以道统制约治统;另一方面,以“通三统”寻求“大一统”,董仲舒以尊天道的王道为本,通过对历史上的制度进行损益,将王道的精神渗入政治与社会,从而为汉立法。

【曾亦】《公羊》学与中国传统政治的重新反思 ——以《春秋》中「微言大义」的讨论···
清中叶以后,随着《公羊》学的再度复兴,刘逢禄借助微言与大义的区分以判分《春秋》三传优劣,开始赋予二者以明确的内涵,而且,此种区分导致了清代今文意识的觉醒,并推动了晚清今古学之间的壁垒和纷争。至康有为,更是将「孔子改制」视为《春秋》的「第一微言」,并成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从而对于传统政治的变革及近代中国的转···

【秦际明】文明共识与近代经学观念兴替
清末民初士人之所以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论及其历史观,与儒家自身的教化观念有内在联系,但儒家对道与法有自身的判断,西方之道、西方之法与中国之道、中国之法是何关系需要我们对中西文明史作更充分的观察。经学作为在世界观、价值观及社会秩序建构等方面的基本共识,既有时代性的思想文化与制度内容,也有超越于时代而体现中华文···

【陈赟】“治出于二”与中国知识谱系的创建
在教化领域中出现的经史的分化以及子学(百家学或诸子学)的兴起,标志着经-史-子知识谱系的形成。经学或六艺学被视为古之道术的正宗嫡传,而子学作为方术,既是对道术的偏离,又可以上通道术。以经学为主体、以史学与子学为羽翼的中国知识谱系,既以经的主干性保证了中国学术精神的深层统一性,又向子、史开放而补充经学,从而形成经···

【张凯】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

【高一品 丁四新】开放的新儒学:郭齐勇先生的儒学观
在我们看来,郭先生的新儒家思想建构和叙述始终遵循两个重要原则:其一,坚持儒学文化的主体性;其二,坚持开放的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其目的是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他的儒学观和儒学思想既彰显了儒学文化的独特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足,作了一定程度的推进。

【蔡家和】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心物关系
心与物的关系,一方面真有主观原则的心,另一方面有客观的物,都是真实的存在,而心能知物,知物所以然之理。心能穷理,格物是不能离于物,面对物而穷其理,而穷理的主词是人,是人心,穷理后则能有知,此为致知,则人心之知做积累工作,做到豁然贯通。

【颜炳罡】轴心文明与齐鲁文化的多重意蕴
齐鲁文化有四重意义:其一,轴心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西周到秦统一这一时期齐国与鲁国的文化;其二,经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主要指秦汉到魏晋流行的齐学与鲁学;其三,行政区位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山东文化;其四,思想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始于轴心时代,以德为先,以修、齐、治、平为目的,主张礼法并治的治理体系与生活方式。

【李明书】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专注”与“动机移位”
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张新民】过化与施教——王阳明的讲学活动与黔中王门的崛起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针对大、小两种传统受众的不同,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学活动,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众,化导移易了民间社会风俗,也培养了不少科考读书士子,构成了王学地域学派的中坚。贵州既是阳明的“过化”之地,也是他的“施教”之区。而黔中王门学者受阳明心学思想的沾溉,主动践行“知行合一”实践哲学精义,不仅人才群体济济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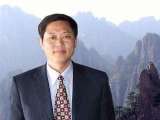
【林忠军】儒家易学传承、创新和重建及其现实意义——以《易传》为视角
今天易学研究当从易学经典出发,借助于传统的象数训诂兼义理等方法,重新解读易学经典和已有研究成果,以客观再现易学文本固有之意为导向。然后在此基础上,以道器关系为出发点,借鉴当代哲学思维方法和学术文化成果及科技知识,促进传统的易学与现代知识深度融合,重建贯通古今中外思想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新的易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