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cover_160_120)
【胡文辉】谈陈寅恪诗及语录
胡文辉先生长期致力于陈寅恪研究,曾出版《陈寅恪诗笺释》,广受学界好评。最近他又推出了《陈寅恪语录》,将陈寅恪毕生治学之精华以“语录体”逐条呈现,并适当地加以按语注解。《上海书评》采访了胡文辉,请他谈谈笺释陈寅恪诗、编纂陈寅恪语录的心得感想。

【杨国强】文化迁流中的“中国本位文化”意识 ——读陈寅恪先生
以陈寅恪先生的学问而论,我们隔了好几层,所以不敢妄发议论。今天应会议的安排在这里略陈一己之见,只能是把陈先生当成中国近代历史变迁中产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象,选取他的三段话,就我的认知所及,说一点个人的理解。

【刘克敌】从大山深处走出的文化世家
算起来这是我第三次到修水了。第一次是在20世纪末,当时从县城到陈家大屋尚无可通机动车的道路,我和当地的一位朋友是在乘坐一段汽车后又在山林中步行了两个小时才来到位于崇山峻岭中的竹塅——也就是陈氏家族的所在地,那所著名的陈家大屋就静静地坐落在一座小山脚下,周围有小溪流过。那一刻的感动我至今记忆犹新,这里是陈宝箴、陈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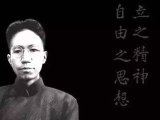
【刘克敌】陈寅恪与弟子的学术交往
对于陈寅恪和弟子的关系,此前研究大都集中在陈寅恪如何指导学生以及学生后来是否背叛老师方面,具体人物则以对蒋天枢、刘节、汪篯、金应熙、周一良等人研究较多。故此处仅论述较少被关注的朱延丰、姚薇元两位,他们入清华后即拜入陈寅恪门下,和陈寅恪关系一直较为密切。

【专访】张求会: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
义宁陈氏源出客家,雍正年间始由福建上杭迁至江西修水,属于被土著士绅排斥的族群,其家族用了百年时间从“棚民”跃升至乡绅;直到陈宝箴中举,才为家族初获功名,以后更因缘际会,成为独掌一方的大员,可说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再到第二代的陈三立,尤其是更下一代的陈寅恪,才算在文化上取得了成功。
-117.jpg!cover_160_120)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纪念陈寅恪逝世五十周年
11月1日至2日,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复建十周年暨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在北京西郊宾馆、清华学堂举行。

【徐国利】陈寅恪对“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

“‘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暨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陈寅恪先生(1890-1969)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成就极其卓著的史学家,对中古史、佛教史和语言学等领域有着开创性贡献,对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158.jpg!cover_160_120)
【刘克敌】“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2019年,是陈寅恪先生,这位20世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20世纪中国文化大师逝世五十周年。
-153.jpg!cover_160_120)
【邵一劭】瞽叟望月,非关圆缺——敬读陈寅恪先生“目疾诗”
值此陈寅恪翁辞世50周年之际,笔者谨依其诗集,“钞胥”其一咏再咏、反复诗写的“目疾诗”,敢乞恪翁纵使长眠,亦“重见天日”“重见光明”。

【周景耀】“假设”与“论理”——张尔田、陈寅恪笺释义山诗的方法论考察
张尔田、陈寅恪关于李商隐巴蜀游踪诸诗的认识存在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李商隐《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诗之系年及寓意的笺释上。陈寅恪以“假设”论史,注重事实的考证与证成“理念”导引下的系统性历史的存在;针对陈寅恪具有现代气质的治学方法,张尔田持质疑态度,他强调“知人论世”与综合事实和经验的“论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非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