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可·阿姆布罗西尼】新冠病毒疫情——世界末日的简短哲学旁注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知道或者不再知道如何有尊严地活着或者死去。现在我们只是死掉,银行帐户注销、电话号码注销、退休金不再支付、重症监护室又多了一个床位。

【罗宾·韦亚德】我的哲学自传
在我的哲学探索旅程和老年反思的过程中,我认识到,我不再是充满渴望的学界知识分子而是更年轻自我的老年版变体。当年进入学界大家庭的普遍理想追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克雷格·克利福德】精彩绝伦却又无足轻重——危机时代的哲学、艺术与运动
在命运的黑暗面占上风的不祥时刻,我们值得牢记的是,哲学、艺术和运动员们精彩绝伦却无足轻重的比赛虽然完全没有必要但是的确高贵无比,而且能让人们都变得高贵起来。我们都渴望找到人生的意义,虽然这可能有些不确定。

【谢青松】人生之乐,莫如自适其适 ——从张廷玉看传统儒者的幸福观
张廷玉(1672—1755年),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清代名臣、著名史学家。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钦选翰林院庶吉士。清康熙时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时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死后谥号“文和”,配享太庙。《清史稿》称:“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

【吕双伟】以华词发其朴学:皮锡瑞的骈文与经学
皮锡瑞中年以前酷爱辞章,对此也颇为自信,曰:“少壮真难再,文章敢自欺”(《四十初度述怀四十韵》)、“绮岁娴词赋,清时拙走趋”(《章江泛船四十韵》)。他重视诗赋、骈、散文且强调入门须正,主张诗、赋师法唐人,骈、散文上溯八代。诗歌宗唐、骈文溯源八代不足为奇,但主张赋法学唐代、散文取法八代,可见其对丽辞的偏爱。中年以后···

【杰西卡·罗格】艺术与道德:苦乐参半的交响曲
本文探讨艺术与道德的复杂关系。

【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虚无主义的春天
后现代人意识到虚无主义有形体却没有灵魂,是个必须依据我们感官享受时代对享乐主义的认识而塑造出的身体。感官时代否认任何形式的首要原则指导,必然枯燥乏味之极。

【阿列克斯·杜伊尔】新冠疫情世界中的真相与异化
本文探讨了新冠病毒疫情及随后的在线生活转变已经促成人们越来越疏远大自然。

【加瑞·考克斯】读摩尔越多,你就越快乐
摩尔认为,在人生的所有东西中,对美和友谊的认识最为宝贵,值得作为目标本身来追求而非仅仅作为追求其他目标的手段。

【西奥多·达林普尔】道德哲学命悬一线
不过,我认为他不应该被绞死就像我认为沙罗威瓦不应该被绞死一样,虽然严格来说,无论你认为他应该还是不应该被绞死,绞死本身并没有应该和不应该的问题,道德哲学的确有些莫名其妙。

【韩鑫】服章之美 承千载风华
4月14日至17日,第四届“中国华服日”将在澳门举行。“中国华服日”由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好者共同倡导设立,于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举办主活动,并在各地举行特色活动,至今已在西安、南京、开封等地成功举办。

【刘剑】也说“父子相隐”
若论起20余年来《论语》研究的热点,“父子相隐”无疑是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之一。自2002年《哲学研究》第2期发表了刘清平质疑儒家“亲亲相隐”合理性(合法性)的文章以后,这场争论便一发不可收,并逐渐聚焦于对“父子相隐”合理性的辩论,而郭齐勇、邓晓芒、梁涛、廖名春等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使这场争论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至今讨论···

【杨朝明】儒家中道传统对现代政商关系的启示
我们现在思考政商关系,思考社会治理问题,是对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说到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我认为很精彩、很独到。我们现在一般把儒家当成一个学派,其实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中国···

【刘余莉】祭祖,对国家对个人,为什么重要?意义在哪儿?
《礼记·祭统》上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治人、治理国家的措施之中,没有比礼更重要、更急迫的了。礼有五个方面,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礼。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这个祭礼是属于吉礼,在五种礼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礼。为什么祭礼这么重要?我们可以从国家的角度,可以从个人的角度,两个方面···

【韩星】挖掘清明节文化意蕴,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清明本来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而清明节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一个祭祖和扫墓的节日。清明祭祀礼俗历史悠久,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据史书记载,清明礼俗源于先秦,形成于秦汉,《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春分……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

【李竞恒】清明节话庙祭和墓祭:后者起源于唐,与家族共同体观念削弱有关
庙祭是一个维系若干死者作为小共同体的结构,体现的是死者死后呈现为家族共同体,无论一个君主或贵族再了不起,他的权力来源和成就也归属于这个死者与生者的共同体。凭借这个共同体的网络结构和历史惯性,个体的权力受到习惯的制约。而墓祭则主要是面对死者这一个具体的个体,是脱离了家族共同体和习惯约束的个体。
-1.jpg!cover_160_120)
【吴钩】清明是如何从欢快的节日演变成伤感的扫墓季的?
又到清明时节,正是慎终追远的时刻。不由想起几年前的旧闻:清明节前夕,四川乐山某居民小区挂出横幅,上写“恭祝全体业主节日快乐”;陕西渭南的电信运营商给四星客户群发节日祝福短信:“您好!清明将至,提前祝您节日快乐”。看到祝福语的小区业主与手机用户都很郁闷:清明节不是祭拜先人、寄托哀思的日子么?怎么可以祝“节日快乐”?

【济楚】舌尖上的清明野菜 ——谈寒食、清明诗词中的蔬菜食俗
唐代,寒食节大致演变固定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或前两天),清明节的种种过节习俗,皆为寒食节所包。而寒食节固定到春季,影响非常深远,比如这篇小文将要提到的寒食、清明采食各种山野蔬菜的食俗,只有在春天才有这些舌尖上的口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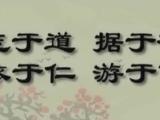
【谢明德】《论语·述而》“游于艺”新解
“游于艺”见于《论语·述而》“志于道”章:“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言简意赅,历来为儒家所重视。艺字的繁体为“藝”,古字作“秇”“蓺”,指种植,如“不能艺黍稷。”(《诗经·鸨羽》)黍稷泛指粮食。从本义引申出知识、技能、艺术等含义。在先秦,艺也称“道艺”。《礼记·少仪》:“问道艺,曰:‘子习于某乎?’‘子善于某乎?’···

【林桂榛】清明谈传统:寒食、上巳、修禊、夏历、火正、炎帝、灶神等
冬至日起算的十月制夏正前3月尾3日是寒食节,再过一周(6—7日)是上巳祓禊除邪活动,寒食与上巳共连约10日,节气正好,暮春温度阳光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