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宗法的意义:《要命的地方》读后
 |
曾亦作者简介:曾亦,男,西元一九六九年生,湖南新化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哲学系长聘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院、经学研究院院长。兼任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儒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春秋公羊学史》《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从素王到真王:刘逢禄〈春秋〉学研究》,主编《何谓普世?谁之价值?》等。 |
宗法的意义:《要命的地方》读后
作者:曾亦(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十一月初八日壬子
耶稣2023年12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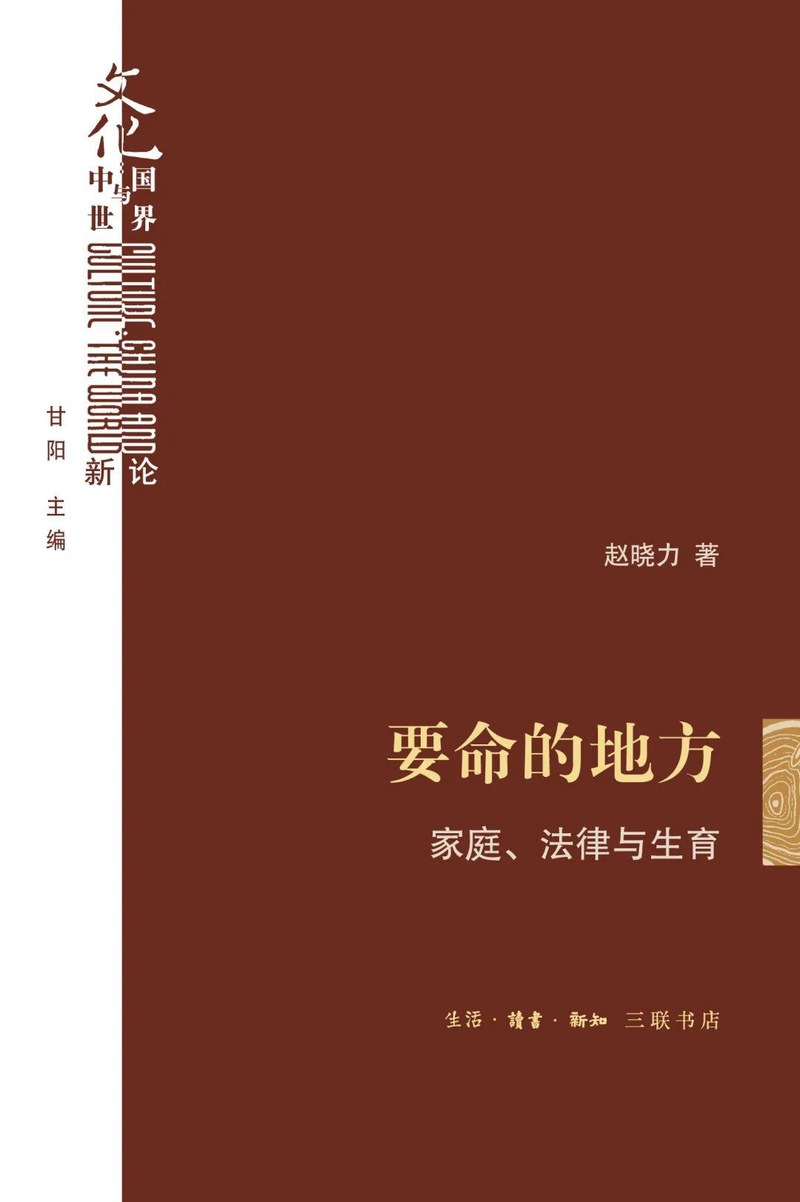
要命的地方——家庭、生育与法律
赵晓力 著
透过眼前这部新书,不难发现《要命的地方:家庭、法律与生育》一书的作者赵晓力教授借助法律学者特有的细腻,通过对几部文学作品的阅读,挖掘出背后的法律问题。其中尤其让我感兴趣的那几篇文章,深入小人物现实生活的分析,讨论了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性,分析现代思想所批判的封建礼教如何影响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
早在2011年,赵晓力教授和我都参加了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在浙江莫干山举办的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当时我俩在前往莫干山的路上,闲谈时聊及当时刚颁布不久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晓力兄对这一司法解释表示担忧,认为新规定将夫妻关系的性质改变为搭伙做生意而已。而我却认为,在传统社会的家庭中,妻子财产本就不曾真正融入家庭财产,家庭财产正是通过父系单侧继承的方式才得以维持其完整性。我随后进一步撰文,结合传统经学的相关理论,并对世界各国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的律条进行了考察,认为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不仅符合儒家传统伦理,而且有利于维持目前家庭的稳定。其实,1950年《婚姻法》中就区分了“共同财产”和“家庭财产”两个不同概念,夫妻财产构成了“共同财产”,但不等于“家庭财产”。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普通家庭谈不上多少财富积累,所以两者的实际差别并不明显。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房价的攀升,两者出现了显著的不同,即基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共同财产”,相较于包含双方父母赠予的“家庭财产”,所占比重越来越小。我认为,2001年修正《婚姻法》及历次司法解释所作出的新规定,正是对当前社会现实变化的深刻反映。最后,我还在那篇文章中指出,如果着眼于未来夫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英美等国家所实行的分别财产制,或许更有利于解释夫妻间在财产分割上的矛盾。固然这种新规定有悖于过去《婚姻法》保护离异女性经济生活的精神,但世易时移,这种保护在当代或许不免不合时宜,且有悖于男女平等的通行观念。
此后,我了解到晓力兄也在继续关注此问题,并与多人有过讨论,发表了不少相关文字。2016年,我读到晓力兄的一篇文章,题名《祥林嫂的问题——答曾亦曾夫子》。文章对鲁迅的《祝福》和《孤独者》两篇小说进行了分析,通常的观点认为鲁迅的这两篇小说意在批判封建礼教造成了祥林嫂和魏连殳两人的悲剧,不过晓力兄却从中读出了礼教正面作用在鲁迅所处时代的遗失。虽然文章标题显是回应我的,但是我一则疏于写作,二则对文学小说素无特别的兴趣,没有当即回应晓力兄的文章。去年晓力兄又写了一篇讨论宗法的长文,我亦产生了回应的想法,只是因为家中多事,始终无暇动笔。直到前几天,晓力兄将新书《要命的地方》寄给我,我翻阅下来,里面赫然就有《祥林嫂的问题》和《魏连殳的自戕》这两篇文章,显系由早些年讨论《祝福》和《孤独者》的那篇文章扩充而来,于是我决心一定要作个回应,了结彼此多年的心愿。
首先,我们还是先讨论一下《祥林嫂的问题》这篇文章。晓力兄在该书后记中写到,通常读者会认为祥林嫂之死是礼教吃人的结果,然而,如果我们深入体现宗法精神的古代法律,不免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不仅祥林嫂的改嫁,更包括贺家大伯的收屋,看似是导致祥林嫂悲剧的根本原因,实际却恰恰违背了封建礼教的精神。按照当时的正统礼法,只要妇人愿意守志,那么族人就应该为贺老六立嗣,这样祥林嫂就不至于再次流落到鲁镇做工,或许也不会有后来的死了。换言之,封建礼教的初衷是保护祥林嫂的,而不是导致祥林嫂悲剧的直接原因。
不过,2014年晓力兄初次发表该文时,似乎还没有深入礼教具体内容层面的探讨,于是我揣测,晓力兄彼时大概认为祥林嫂悲剧的根源仍在于妻子不能继承丈夫的财产,才有了贺家大伯收屋的举动。相反,如果按照现在民法有关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妻子不仅能够占有共同财产的一半份额,尤其在夫死无子的情况下,更是可能继承超过一半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自然就不会有祥林嫂的悲剧了。然而,值得追问的是,虽然祥林嫂一类的妇女没有悲剧了,夫家的人却可能会蒙受更多的不幸:贺老六的财产是祖上传下来的,而不源于夫妻的共同劳动,一个外来的女子凭什么分割夫家世代积累下来的财产?
《要命的地方》附录中还有《女儿也是传后人》这篇学理性很强的文章,充分体现了晓力兄近年在经学方面的学养和思考,代表了晓力兄在理论上的自我完善。近些年来,浙江出现了“两头婚”这种新现象。晓力兄大概从这种现象中看到了男女平等继承的某种因素,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即符合古代中国法律关于妻子“承夫分”的规定,因而似乎对“两头婚”颇为关注。其实,这种现象违背了晓力兄此前的主张。基于夫妻共同生活而形成共同财产,由夫妻二人平等分割,这反而接近英美分别财产制的做法。晓力兄在文中尝试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即追溯到《公羊传》“为人后为之子”的说法,认为这正是古代宗法制的体现,声称从理论上“为人后者”不局限于男性,而“两头婚”正是贯彻了“女儿也是传后人”这一双系继嗣的精神,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宗法制的返本开新”。
在追溯双系继嗣历史渊源的过程中,晓力兄注意到,早在明律中,已有妻子“承夫分”的明确规定,尤其是从近百年来种种婚姻家庭法规的演变历史来看,“两头婚”的出现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其实,妻承夫分的法律规定,就现存古代法律文献来看,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的《户令》:“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聘财之半。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其后,宋《户令》也有同样规定。不过,这些规定不同于民国以后的法律精神,即未赋予妻子以完全的继承权,而是有条件限制的。首先,夫死无子,妻才允许“承夫分”。其次,妻不得改嫁,须在家守志。最后,妻必须为亡夫立嗣,并将代为继承的财产转移给嗣子。显然,这些前提条件都是出于延续男性宗祧的目的,与近代基于保护妇女精神的女子继承权用意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本质上说,妻虽然允许“承夫分”,但并不是夫家财产的所有者,而只是代为管理者,相当于现代法律讲的“代位继承”。
可见,古代法律中关于“妻承夫分”的规定,目的仍然在于夫家财产的保护和宗祧的延续。至于“两头婚”的性质,实则不同于目前《民法典》所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下的相互继承,反而近于欧美的分别财产制,虽然具有双系继承的形式,却是为了维护夫妻各自婚前家庭财产的完整性和姓氏的延续。而且,这种制度很大程度上依赖能诞育两个以上子女的偶然概率,尤其偏好男性子嗣,毕竟男子对于家庭财产的保存和增值有着更大的优势。
关于妻承夫分的古代法律规定,本质上是宗法制的大宗收族功能废弃后的补救办法,实非西周宗法的本意,或许起源较唐律更早,毕竟早在春秋中晚期,原初的西周宗法就已逐渐崩溃了。晓力兄大概看到了目前家庭财产继承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对于“两头婚”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新探索,抱有一定的理论期望,并为之溯源到某种历史合理性,不过这种理论期望能否实现,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罢了。
那么,古代宗法的意义何在呢?清代学者程瑶田认为,宗法之道在于“以兄统弟”,即在亲亲之情中建立尊尊的原则,其目的则在抟聚诸亲属为一尊卑有序的血缘共同体。因此,对于魏连殳来说,作为承重孙,却承受着远离亲情的孤独,但对于维系整个共同体来说,个体的孤独却是必要的牺牲,毕竟人类不同于动物,有着超越血亲之上的更高追求。并且,我们最后看到,当继祖母去世时,魏连殳的痛哭又实现了宗法对承重者的情感要求,此时,为人后者与所后者在情感上成为真正的母子了。
(责任编辑:近复)
【上一篇】陈明 著《江山辽阔立多时》自序暨目录
【下一篇】【丰家雷】儒商的现代市场价值
作者文集更多
- 曾亦 李新 点校《春秋集传 春秋师说》··· 02-04
- 【曾亦】刘逢禄《春秋》学著述再考 10-02
- 曾亦 著《从素王到真王:刘逢禄〈春秋··· 12-29
- 曾亦 陈姿桦 著《古人的日常礼仪》出版··· 03-23
- 【曾亦】宗法的意义:《要命的地方》读后 12-22
- 【曾亦】《春秋》为“刑书”——兼论中国古··· 12-21
- 【曾亦】《公羊》学与中国传统政治的重··· 12-18
- 【曾亦】经学与哲学之间——读方朝晖《中··· 06-15
- 【曾亦】“亲尽宜毁”与“宗不复毁” ——论··· 08-31
- 【曾亦】严父莫大于配天:从明代“大礼··· 06-22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