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jpg!cover_160_120)
【谈火生】治体论与政体论是对立的吗?——任锋新著《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读感
中西方都有“治体论”,但各有特色。我不赞成将“治体论”作为“政体论”的对立物,它们之间不应该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相参照的关系,它们完全可以在相互观照的过程中丰富自身。

【(美)安靖如】儒家领袖与儒家民主
儒家民主主义者认为,如同现代儒家政治体必须从君主制转变到民主制一样,必须对儒家政治领袖的角色进行反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儒家必须摈弃传统儒家视野下的领袖观。
-8.jpg!cover_160_120)
【陈东】释奠制度与孔子崇拜
“释奠”一词原出自《礼记》,是指在学宫中举行的祭祀“先圣先师”或“先老”的一种仪式。魏晋时期太子每通一经之后的祭祀,以及太学开学时的祭祀对象开始集中转向儒家先圣先贤。

【专访】康晓光:热闹的公益不等于好公益
康晓光认为,当下中国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多元化中重建主流价值,而非简单拒绝多元化。“建构路径、寻找方法不能只停留在纸面和书本,而是要真正把项目设计运营、组织架构、团队成长实实在在地落地,体用打通、体用合一,让这些有益的价值观对行业产生有效的推动和影响。如果我们的交流永远停滞在分析问题层面,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杨国利 杨国志】本体论和康德道德论视野中的儒学之孝
孔子对孝文化的杰出贡献在于创新性地在关系性孝中引入了公平与平等思想,并为孝文化奠定了本体论的根基,因此孔子不仅是个守旧守成的文化传承者与批判者,更是个开思想新篇的理论创新者和修正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不仅是儒学之孝的本体与实体所在,也是一种自然法则与定言命令,由此决定了儒学的孝是具有科学性的伦理···

【方朝晖】仁爱、兼爱还是博爱?
各大宗教的博爱思想建立在彼岸取向世界观基础上,墨家的兼爱虽接近于博爱,但因为没有彼岸世界观,所以不现实。中国文化建立在此岸取向世界观基础上,故适合于仁爱之道。这是儒家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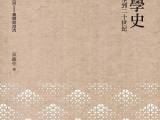
【衷鑫恣】以妓女羞名儒:从明清小说家到五四文人的反儒套路
自古以来,名儒与妓女(艳女)的故事是文学与民间热衷的话题。

【余东海】暴君和革命
桀纣和嬴政都是著名暴君,但性质大不同。桀纣之暴是个体性的,没有相应的极权文化背景和制度基础。君王之暴固然会败坏礼制,却也受到制度一定程度的制约和各级官员不同程度的抵制。嬴政之暴则是道德性、文化性和制度性的统一,由邪说恶制暴君组合而成的极权暴政,罪恶全方位,灾害无止境。

【李明辉】如何继承牟宗三先生的思想遗产?
牟先生就像古往今来的大哲学家一样,留下一大笔思想遗产,唯善学者能受其惠。善学者既能入乎其内,亦能出乎其外,但此非易事。能入乎其内,而未能出乎其外者,犹有所得,胜于在门外徘徊张望者。

【杨国荣】略说浙学
事实上,作为主流中的支脉,“浙学”每每通过挑战主流思想的方式,显示自身的学术品格:王充挑战当时主流的经学,事功学派挑战主流的儒学,王阳明挑战正统的理学,章学诚挑战主流的乾嘉学派,等等。直到近现代,马一浮的思想也蕴含着对西学思潮的某种挑战。可以看到,以有别于主流的独特方式延续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构成了浙学的个性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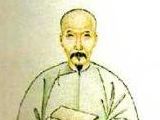
【李圣华】清代朴学中的“浙派”
清代浙学在经学、史学、小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近三百年清代学术发展演变深具影响。

【彭国翔】挣扎与孤寂:牟宗三的爱情世界
牟宗三以哲学家名世,但他并不只有冷静的理智而“太上忘情”。只要阅读牟宗三的相关文字,就足以感受到其人情感之强烈与真挚。

【李景林】“通过经典的解释做一个经学家”——追念余敦康先生
余先生率真谐趣,其言谈文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此其表;但他又常于嬉戏谐趣中见出严肃,透显一种道义担当的精神,此其里。这个担当的精神,就是体现在其对中国文化学术的一种“文化理念、价值关怀”,一种对学术人生“自我”的追寻。这种文化理念和价值关怀及及其对“自我”的追寻,运行在其言谈与论著里,使他所做的工作,超越了时下一···

带着困惑和焦虑离开——余敦康先生追思会在京举行
斯人虽逝,精神永存。余敦康先生被称为当代魏晋名士,他一生追求真理,为人真诚洒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思想遗产,对于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和现代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整理和发掘。

【李细成】康有为谭嗣同弘扬儒家入世精神的两个维度
为了应对基督教的理论挑战,康有为刷新了传统儒学入世天游的修道空间,谭嗣同则激活了传统儒学入世永生的成道时间,他们知行合一地光显了传统儒学入世立功的弘道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