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晓丽】从“阴阳”到“德刑”——董仲舒德主论的建构与证成
通过天道阴阳与《春秋》经典解释学,董仲舒从三个逻辑向度建构与证成德主论(“德主刑辅”):在“阴阳—德刑”向度,将阴阳关系调适为“尊卑”“贵贱”形态,为德刑的“主辅”位置提供本体论根据;在“阴阳—经权”向度,将宇宙真理借《春秋》大义转化为历史时空中的可操作性原则;在“经权—德刑”向度,论证德的优位性及其实现方式。

【韩星】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爱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作为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爱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在儒学历史上具有重要贡献。《春秋繁露·俞序》说“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指出孔子作《春秋》的主旨是批判当时社会缺乏仁爱。董仲舒认为,《春秋》以仁为本体,倡扬德治仁政,反对武力服人,“《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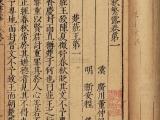
【刘国民】“崇儒更化”:西汉时期的文化建设 ——兼论董仲舒《天人三策》的重要意义
每一民族在发生巨变的时代,都会面临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而文化建设是政治建设的基础,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时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化建设,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邓红】董仲舒与汉武帝:儒政关系中的君臣离合
在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关系中,汉武帝是因,董仲舒是果,武帝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和选择权。董仲舒在《对策》和著作中为汉武帝设计和提供了君权天授、天道化纲常伦理和儒者治国的方案与蓝图,企图将汉武帝指向的“大一统”体制神圣化、系统化、恒久化。这是他在“大一统体制面前的主动选择”,是儒家“学而优则仕”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

【李宗桂】王博著《究天人与通古今:阴阳五行视野下的董学新阐》序言
董仲舒思想研究是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的重点,近年在各方面力量和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成为热点,是当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前沿问题。

【尔雅台】董仲舒天人三策(三)
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尔雅台】董仲舒天人三策(二)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尔雅台】董仲舒天人三策(一)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jpg!cover_160_120)
【邓红】董仲舒的五行说和十月太阳历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等文章中,为了将五行和阴阳四季一年完美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五行每行平均配当“七十二日”的说法。这个“七十二日”的说法可能是受到了《管子》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十月太阳历。

【代春敏 王文书】千年回响:诗歌里的董仲舒 ——(唐)张说《酬崔光禄冬日述怀赠答》
太极殿②众君子,分司洛城。自春涉秋,日有游讨。既而韦公③出守,兹乐便废。顷因公宴,方接咏言。崔光禄述志论文,首贻雅唱。诸公嘉德叙事,咸有报章。若夫盛时、荣位、华景、胜会,此四者古难一遇,而我辈比实兼之。至于精言探道,妙识发义,戏谑而逢规戒,指讽而见师表。益过三友,岂易得乎?谓膏泽傍润,芝兰久袭,韦公近之矣。以文···

2021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
今天上午,2021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研讨会在衡水开幕,来自全国各地从事董仲舒及儒学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共计40余人参加会议,并围绕“儒学复兴从衡水走来”主题进行研讨交流。

【秦际明】元作为治统的本原与方法 ——董仲舒“元”论新解
董仲舒之政治思想以人为本,以教为治人、成就人的根本之道。董仲舒推阴阳以立制度,以天统人,而寓教于其中。从形式上看,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是天,如若问天之所欲为何?其答案是元。元是一切追问的最终答案,因而是最原初的出发点。天地有天地之元,人有人之元,万物亦有其元,元是一切存在的本质,亦即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与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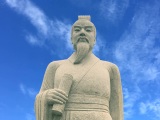
【高瑞杰】汉代三统论之演进——从董仲舒到何休
汉儒董仲舒创三统说,强调圣王受命应天,必须依据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实兼礼仪象征义与实质变革义;又将《春秋》纳入三统谱系中,以《春秋》当新王,存商、周为二王后,并匹配一整套政教制度设计,使得《春秋》可为汉治所取法。然其强调汉治亦当用夏教,实无法摆脱其失道覆亡之命运。经过纬书、《白虎通》诸说之推阐

【李慧子】董仲舒对孟荀思想的统合
董仲舒在统合孟荀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自身儒学体系。在天人思想上,他突破荀子天之不可畏的观点,通过天生万物、天人感应论来充实孟子“天之所与我者”的表述,重建天的威严,为人间伦理确立天道基础。在人心论上,他将孟子“四端”之心说与荀子“心好利”说相结合,提出“心有贪有仁”,强调心具有抑恶扬善之“栣”的功能。

【周灏】《春秋繁露》中的“权变”观念及其元伦理学分析
“权变”是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重要观念。从“权变”的定义、目的、范围和精神来看,其核心内涵是臣子拥有判断是非的自主性,行权的要旨在于君臣能否各自承担责任、履行义务。“权变”观念主张追求高尚的价值,拒斥符合普遍法则的绝对律令,在元伦理学上,其性质属于目的论式而非义务论式的伦理学。因此《春秋繁露》支持的是一种相对意义···

【刘丹忱】董仲舒“大一统”理论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赋予其政权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以解决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性及国家文化认同的问题。两汉四百年的空前统一更使大一统思想固化为民族心理,中华各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董仲舒确立的“大一统”学说为中华民族长期自在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撑,使各···

【宋大琦】董仲舒天命政治观与孔孟之道的矛盾与兼容
以董学为代表的汉代天命政治学是一个先构建了天学体系,再将人世政治纳入进去的理论,这与孔孟直接从人性要求出发的政治思想是矛盾的。董学舍弃孔孟的思维方式,继承孔孟的价值主张,用天人同构之理将人性纳于天道,用神化孔子、以孔子学说为代天立言的方法将孔孟之道纳入天人框架中,事实上是用天学体系整合了孔孟学说,形成天命政治···

【迟成勇】董仲舒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综合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继承和发展先秦儒学,创立汉初新儒学,实现了儒学的第一次综合创新,并使儒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居于国家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思想,同时也开启了宋明新儒学之先河,对儒学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喻中】依经治国:董仲舒开创的法理命题
从汉至清的中国则是“经治时代”的中国,亦即“经治中国”。“经治中国”实行“依经治国”。“依经治国”是由董仲舒开创的一个法理命题,同时也是从汉至清两千年间中国固有法理学的主题。

【黄玉顺】义不谋利:作为最高政治伦理 ——董仲舒与儒家“义利之辨”的正本清源
董仲舒的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惯常被误解,以为它是对于社会全体成员的一条普遍的道德要求;其实,它只是特别针对政治权力与政治精英而言的一条特定的政治伦理。“义”与“利”的对立乃是基于两种主体的对置,即“君”与“民”或“官”与“民”的对置,意味着:民众谋利乃是天然权利,权力谋利则是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