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遐龄】董仲舒礼学思想初探
董学为《春秋》学,按某个维度看,相当于今日的历史哲学;公羊学,是宗教性历史哲学,即王道学。董子的历史使命是重修王教复旦大学,于六艺中特重《春秋》。他响应时代的要求,探讨治国思路与治国活动内涵的宗教性——合乎天命,试图从《春秋》学中整理出礼学的基本结构——国家体制包含“天、君、民”三个层面。当代学者多半未把天看作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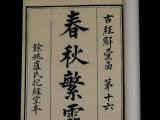
【耿春红 刘玉敏】《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智慧观解读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专辟一章论说智慧,这就是“必仁且智”篇。文章分三段从三个方面对智慧进行论说,即智慧的重要性及在选材用人方面的不可或缺性、何谓仁、何谓智。董仲舒认为,仁,指心理情绪,要对心理情绪进行管控,行为、结果才不会出现偏差;智,是指思维的规范性、判断的合理性及行事的恰当性三者的有机统一,含理性和实践的···
.png!cover_160_120)
【王淇】董仲舒类感思想的建立及其目的
中国哲学史上,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同类”的观念,建立起更普遍的相互感通的学说。董仲舒是其中第一个完整而成体系地论述同类相感运行机理的哲学家。他从数目、性质和位置三方面重新诠释了“同类”观念,以此为基础建构了天人之间同类相感的学说。类感学说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官制、分配制度、任德不任刑的主张提供天道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为···

【干春松】从天道普遍性来建构大一统秩序的政治原则——董仲舒“天”观念疏解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系统阐发了自己的“天命”“天道”“元”等概念,并由此展示出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儒家如何借助汉初自然化的天人观念来建构其普遍性的政治原理。在此基础之上,董仲舒进一步借助“元”观念形成了天道对政治秩序、伦理秩序的支撑,完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转折。
-10.jpg!cover_160_120)
【曹迎春 崔明稳】“聚力融合 协同发展 ——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2020学术年会暨儒商···
2020年12月19-20日,“聚力融合协同发展——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2020学术年会暨儒商文化研讨会”隆重召开。此次年会的主旨演讲、儒商论坛、分组研讨都是紧紧围绕“董仲舒思想”和“儒商文化”两个主题进行。关于董仲舒思想,主要围绕其主要思想、历史影响、现代价值以及董子文化的普及开发、董子故里的地域文化等进行研究;关于儒商文化,主要···

【张俊娅】董仲舒的“春秋”观 ——观念史与史学史的考察
《春秋》在先秦包含三个概念,一是百国春秋,二是孔子所修的《春秋》,三是《左氏春秋》。西汉董仲舒是春秋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春秋》概念是为《春秋》“正名”的重要里程碑。探究发现,董仲舒是一个纯粹的公羊学家,他所说的《春秋》是指《春秋》经与《公羊传》;他的学说中有《左传》因素,是因为他视《左传》为史料;他的学说中···

【余治平】“存王者之后”以“通三统” ——公羊家建构王权合法性的一个特殊视角
《春秋公羊传》《礼记》较早总结出上古中国政治文明“存二王之后”的传统。礼遇前朝的遗老遗少,赐与其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保留先王之子孙后裔、政教礼制法度、历书体系,以体现时王也是受命之王,尊重先圣,分享国土,“不敢专”,不为一家一姓所私占。其效果则能够把新兴政权纳入历史谱系,展示自身道统与前朝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黄朴民 李櫹璐】董仲舒“天人合一”的 “理性”内核与制衡精神
中西历史文明自前轴心时代开始,就进入了有所差异的路径。与西方的政治二元结构不同,商周以来,政治统治上的重心就落实到一元结构,秦汉帝国时代以降,这种结构性特征更趋于强化。其正面意义不容否定,但弊端的存在也是事实。如何制约专制君主权力的无限膨胀,在帝国权力运作中达到适当的平衡,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程苏东】《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

【赵秀金】董仲舒“天人三策”应在元光五年辨正
“天人三策”发生的时间,必须立足文本和史实进行考辨。汉武帝对董仲舒的策问,与元光五年对公孙弘的策问主旨一致,而且“天人三策”是同一主旨的问答系列

【孙兴彻】董仲舒的人间观
董仲舒的人间观以“性三品说”“知识论”“教化论”为主要内容。他将“性”与“情”放在同等重要的层面,其人间观以“性情论”为核心。

【王江武 王康】董仲舒的革命思想
“汤武之禁”后以何种方式继续言说儒家的“革命”理论,成为汉代儒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王博】阴阳五行与董仲舒“官制象天”学说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了独具特色的“官制象天”学说。“官制象天”以天人相副为前提,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为纵向层面上天之数与官之制有着严格对应,以三、四、十、十二、百二十等天之数构建起百官系统;其二为横向上五行与五官严格对应,以五行生胜为依据构建起彼此共生又相互制约的五官系统。第一个系统纯为理想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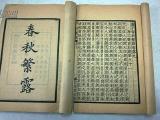
【樊志辉 郑文娟】时间意识下的天道与人道 ——对张祥龙现象学视域下《春秋繁露》 ···
从张祥龙所提出的现象学视角入手,通过对《春秋繁露》的研究,梳理出其中的时间意识。“元”作为《春秋繁露》的核心范畴,其本身就内蕴了时间,进言之“元”即是时间的发端。推而论之,天道、阴阳以至于四时、五行皆为时间的展开,人道之社会历史合于天道,同样是随时显现的时间本真。《春秋繁露》之天人关系即是在时间上的统一,而这样一···

【郑朝晖】论董仲舒的“馀义”言说
《春秋繁露》是典型的融合性文本。董仲舒能够将不同学派的思想资源融为一体,与其"馀义"言说方式有关。馀义言说是"以比贯类、以辨付赘"的方法,亦即通过连环问答、数理描述、天人对话揭示人情与辞义、天志与名号之间的同一性。不同学派的思想资源能够融为一体,正是借助于"比例法"与"正义法"。

【杨运筹】春秋“王鲁”说刍议:以董仲舒为中心
董仲舒等汉人论定“王鲁说”一方面是上探孔子“缘鲁以言王义”的微旨,另一方面是要处理汉代秦而兴的合法性问题。而在具体处理汉朝代秦而兴的解释学说时,“三统循环”之外尚有“五德终始”,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彼此冲突。出于勾销秦统,为汉立法的意图,董仲舒采用“三统循环”而不取“五德终始”。

【黄玉顺】董仲舒思想系统的结构性还原 ——《天人三策》的政治哲学解读
“灾异”说是理解董仲舒思想体系之整体结构的核心枢纽,因为他正是通过解释“灾异之变”现象来臧否政治而引申出自己整个思想系统的三大板块及其关系。灾异说的政治理想却是皇权帝国之“大一统”的完善,这恰恰是对前述儒家神圣代言人的主体独立性的解构,从而也是对“灾异”说本身的解构,因而促使后世儒家转向“内在超越”。

【郑济洲】论董仲舒对“天下为公”理念的制度设计——从五四“反传统”的反思说起
五四的“反传统”视域往往用“支持专制”来定性孔子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实际上“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截然不同,前者是古代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的治世工具,而后者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天下为公”。董仲舒制度化“天下为公”的努力受到了古代帝制与五四思潮的双重否定,古代帝制“霸王道杂之”的治世理念限制住了儒家“君臣共治”的理想,五四思潮所···

【吴飞】董仲舒的五行说与中和论
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春秋学的文字与阴阳五行的文字大致上各占一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余治平先生的《唯天为大》与《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两书分别论述这两个方面,对此后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笔者以为,对阴阳五行体系之义理的综合,是董仲舒学说的哲学基础,虽已有不少研究,仍有必要深入其中,特别是其中的···
-50.jpg!cover_160_120)
【王涵青】从孟子与董仲舒的“仁-义-利”结构论道德实践的主体价值抉择
从道德实践的主体价值抉择的面向上来看,在对孟子与董仲舒的“仁-义-利”进行分析后,能更进一步地将此两有别但不矛盾的结构进行整合,重新审视儒家的仁义关怀,让过于强调个体与自我的现代人重新回到世界之中,展现出一条重新连结自我与他者之路,这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思考道德实践的主体价值抉择之可能性与动力的可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