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奎凤】张岱年论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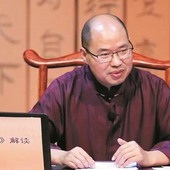 |
翟奎凤作者简介:翟奎凤,男,西元一九八零年生,安徽亳州人,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曾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任教(2009-2013),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工作(2010-2012),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以易测天:黄道周易学思想研究》等。 |
张岱年论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作者:翟奎凤(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中国哲学史》2025年第5期
摘要:在晚清近代,面临空前生存危机的中华民族焕发出强大斗志,自强不息、刚健奋进的精神格外突显。受时代影响,张岱年早年关于中华文化的讨论也是特别强调“自强不息”、刚毅进取精神的重要性,罕言“厚德载物”的包容、和平精神。1980年代中后期,张岱年提出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到了1990年代,张先生特别突显“厚德载物”精神的重要性,他认为世界各伟大民族皆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但“厚德载物”的包容、和平精神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自强不息”彰显了民族主体性、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张先生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起来。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辩证统一的,立足于新时代的民族精神,如果继续借用《周易·大象传》话语,可以吸收《周易》下经咸恒两卦的大象辞,将其表述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虚受人”“立不易方”。
关键词: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爱国主义 主体性 和平性
关于民族精神的讨论,大概始于1900年,在1930-1939年期间特别是1934年前后相关讨论非常密集,不少人把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与发扬民族精神结合起来。1980年代以来,关于民族精神的讨论又活跃起来,如刘纲纪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包括“理性”“自由”“求实”“应变”四大精神(1),谢幼田从“直觉是中国思维的出发点”“和谐与整体性”“中庸的方法与原则”三个方面论及中华民族之精神(2),等等。在这些讨论中,张岱年先生的观点影响最大,张先生认为《周易》乾坤两卦《大象》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最能代表中华民族之基本精神。对于张先生的民族精神观,迟成勇等人曾做过解读与阐释(3)。本文与迟成勇以及相关研究的角度不同,侧重考察张先生这一论断的提出过程,分析其观点的前后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就民族精神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思考。
一、“自强不息”与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乾坤为《周易》之门户,64卦可谓皆由乾坤两卦交合变易而来。《乾·大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大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坤两卦虽很重要,但在古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似并未引起特别关注。这两句话特别是“自强不息”的“崛起”是在近现代。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生存危机,一批批有志之士前赴后继,试图通过变法图强来振兴中华。“自强不息”成为这一时期振奋国民精神的响亮口号,在晚清民国很多报刊的醒目位置,经常有此四字题词,各界演讲和学人专文也常以“自强不息”为主题主旨,不少高校甚至中小学也以“自强不息”为校训、学训。由于积贫积弱、落后就要挨打的血的教训,在近代文化中,我们突出强调了“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相对地,“厚德载物”提得较少。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发表论君子的演讲时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最能概括君子修为的基本精神。1920年,《清华周刊》第205页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题词,1931年清华《消夏周刊》第7期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题词。清华校训源自梁启超论君子的演讲,除此之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近代社会文化中很少并提。这也可以理解,在近代中国,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首要的是“自强不息”,通过变革、斗争来实现独立自主,摆脱“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显然,“厚德载物”之平和包容精神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是不合时宜的。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这种看法影响广泛,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张岱年首先提出来的,更不清楚张先生是在什么年代提出的。对张先生这一观点的具体提出过程作一考察是必要的。
自1933年大学毕业始,张岱年先生曾长期在清华任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对张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时代影响下,张先生早年也是只强调“自强不息”精神的重要性。张先生在1932年《辩证法与生活》、1933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两文中只是偶尔提到“自强不息”,并未作特别强调。1934年,张先生在《中国思想源流》一文中开始强调说“《易传》也是发挥宏毅哲学的”,“自强不息”“刚健中正”“表出了中国固有精神之精髓”(4),认为“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中国要再度发挥其宏大、刚毅的创造力量”(《全集》第一卷,第199页)。1935年,在《西化与创造》一文中,张先生认为“刚健的态度,主自强不息,生生日新,宰制自然”“我们所要发扬的原有的卓越的文化精神,乃是原始的刚健精神”(《全集》第一卷,第250-251页),这里将刚健自强视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之脊梁。在1936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人生论”部分论及《大象传》道德修养时,张先生指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实是《象传》中的人生思想之中心观念”(《全集》第二卷,第347页)。1944年,在《天人五论》“品德论”中释“勇”时,张先生指出“勇亦曰刚,亦曰毅,亦曰强”“自强不息,可谓大勇。力强足以胜艰难,志坚足以抗险阻,然后为勇”(《全集》第三卷,第214页)。总体上看,1949年以前,张先生感于民族时代,特别强调宏大、刚毅、自强、勇健之精神,这是一种人格精神,也是一种文化精神。
1980年以后,张先生继续强调“自强不息”的重要性,自强不息不仅是我们的文化精神,也是民族精神。1982年在《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张先生以“刚健有为”为中华文化四大基本精神之首,指出“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全集》第五卷,第420页)。1984年,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中,张先生指出“在《易传》所宣扬的‘刚健’‘自强不息’的思想的熏陶影响之下,中国历代优秀的知识分子表现了三个方面的优良品格和作风:第一,诚挚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第三,刚强不屈与不良势力进行斗争的精神”(《全集》第五卷,第668页),这里张先生视爱国主义为“自强不息”的首要精神。1985年2月,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中指出“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应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态度”(《全集》第六卷,第42页);同年7月,在《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文指出“中华民族有一个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传统,同孔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全集》第六卷,第86页)。至此,张先生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时主要还是强调自强不息,尚未并提“厚德载物”。
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族精神的提出
张先生关于民族精神的讨论,一定意义上是在1980年代“文化热”的大背景下来展开的,与其文化上主张“综合创新”说是同时期提出的,这些都是在1984年之后的思想。张先生晚年回忆说“1983年以来,国内出现了讨论文化问题的热潮,这是80年代学术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全集》第八卷,第102页),“1984年以来,国内文化热兴起,我明确提出‘综合创新’的观点,并且着重揭举了‘民族精神’的问题,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可称为‘中华精神’,其主要内容可以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表述。这些见解近几年来已受到人们的注意,并且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是我感到欣慰的”(《全集》第八卷,第308页)。
张先生首次明确自觉地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大概是在1985年8月24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上《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演讲中,他认为“应该肯定,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多年,必然有其优秀传统作为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现在我们要达到对于民族精神的自我认识”;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思想基础”(《全集》第六卷,第90页)。但是张先生对此没有进一步详谈,到了1986年,才对此作了更多展开。
1986年4月24日,张先生以《中国文化的回顾与前瞻》为主题在北京师范大学作报告,他认为《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对中国文化起到促进作用,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
天体、日月、星辰,昼夜运行,今天太阳从东方出来,明天太阳也一定从东方出来,太阳不会懒惰,永恒运动,许多行星也是这样,人就应自强不息,永远前进,勉力向上,决不停止。我认为自强不息观点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厚德载物”,大地包容万物,兼容并蓄,什么东西在地上都可生长,人应胸怀广大,无所不容。这些思想观点,在民族关系上,表现特别明显。一方面,中华民族是坚强不屈的,不向任何外来势力屈服,坚决保卫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反对扩张主义,我不向你扩张,你也不要向我扩张,互相保持和平,“协和万邦”。坚决保卫民族独立,就是爱国主义的传统,这是非常可贵的。(《全集》第六卷,第146-147页)
“自强不息”就是要像日月星辰那样周流不息、永远前进,“厚德载物”是像大地那样包容万物、胸怀广大。这是论君子人格修养,拓展到民族精神上,就是一方面独立自主、坚强不屈,另一方面睦邻友好、爱好和平。这里,张先生也把“自强不息”与爱国主义、保卫民族独立联系起来。
1986年4月28日,张先生在中央党校作学术报告《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其中第三节谈《国民性与民族精神》,他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延续发展,必然有自己的精神支柱,这个也可以叫做民族精神。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全集》第六卷,第136页),而《易传·大象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在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是自强不息,永远运动,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另一方面也要包容多样性,包容不同的方面,不要随便排斥哪一个方面”;这两句话在个人生活上也有表现,但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自强不息,就是坚持民族独立,决不向外力屈服,对外来的侵略一定要抵抗,保持民族的主权和独立。自强不息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拼搏精神’。同时还要厚德载物,胸怀广大,不去侵犯别人,保持国际和平。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全集》第六卷,第137页)。简单来说,这种精神就是既不受人欺,也不欺负别人,是一种独立、自强、和平的精神。这与在北师大的讲话基本是一致的。
1986年8月2日,张先生在青岛中西文化讲习研讨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再次谈及“国民性和民族精神”问题,他说“一个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在西方,古希腊文化表现了希腊精神,法国人民强调法兰西精神,德国人民宣扬日耳曼精神,东方的日本也鼓吹大和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基本的主导思想意识可以称为‘中华精神’,‘中华精神’即是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而“‘中华精神’集中表现于《易传》中的两个命题”:
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努力向上,绝不停止。这句话表现了中华民族奋斗拼搏的精神,表现一种生命力,不向恶劣环境屈服。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在政治生活方面,对外来侵略决不屈服,对恶势力决不妥协、坚持抗争、直到胜利。在个人生活方面,强调人格独立。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讲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代儒家强调培养这种伟大人格。这种精神,应该肯定。《易传》中还有一句话:“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要有淳厚的德性,能够包容万物,这是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方有宗教战争,不同的宗教绝对不相容。佛教产生于印度,却不为婆罗门教所容,结果佛教在印度被消灭了。在中国,儒学、佛教、道教彼此是可以相容的,这种现象只有中国才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个是奋斗精神,一个是兼容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点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全集》第六卷,第168页)
这与同年四月份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在观点上基本一致,在一些细节表述上更为丰富了,同时也有一些新的思考,比如说这里强调了“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是“只有中国才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儒者的人格精神,也是我们的文化精神、民族精神。1986年9月24日,张先生在董仲舒思想研讨会上发表《关于文化问题》的讲话,他说民族精神“是我提出来的”,“妨碍民族发展的那不叫民族精神,能够促进民族发展的才叫做民族精神”(《全集》第六卷,第190-191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自强不息是积极奋斗、不畏强权的精神,厚德载物是包容宽容、“和而不同”的精神。1986年9月11日,在《〈中华的智慧〉前言》中,张先生指出《易传》虽作于战国,但仍是孔子学说的发展,“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既是人生原则,也是民族精神,体现了儒家的智慧。
从1986年开始,张先生在自觉地思考并凝练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在4月、8月、9月报告的基础上,1986年底,张先生就此问题发表专文《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他指出“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一个民族应该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全集》第六卷,第223页)。而《易传》古来主流认为是孔子作的,有着极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乾坤两卦又是《周易》六十四卦的纲领和门户,其《大象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天地精神又能鼓舞人心、激扬奋发,在张先生看来,以其作为民族精神是最合适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是一体的,张先生强调“中华民族必有作为民族文化的指导原则的中华精神。古往今来,这个精神得到发扬,文化就进步;这个精神得不到发扬,文化就落后。正确认识这个民族精神之所在,是非常必要的”(《全集》第六卷,第225页)。
1988年2月20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演变及其发展规律》一文中,他再次论及民族精神:“广义的民族精神指一个民族所有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思想意识,狭义的民族精神专指能起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的精粹思想”(《全集》第六卷,第356页),而《易大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体现了这种精粹思想。张先生又说:
传说《周易大传》是孔子撰写的,因而在二千年的学术传统之中,《周易大传》具有崇高的地位与广泛的影响。据近年史学家的考证。《周易大传》应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著作。《周易大传》的这两句话,表达了当时的进步思想。事实上,“自强不息”是战国时代华夏人民奋斗精神的反映,“厚德载物”是当时华夏人民宽容精神的反映。这种精神在秦汉以后流传下来。中国人民对内反抗暴政,对外反抗侵略,表现了坚强的奋斗精神。同时对于不同的宗教采取兼容的态度,向来没有发动对外侵略,表现了宽容精神。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随时代的变迁而有消有长、有进有退。当民族精神发扬充盛之时,民族文化就发展前进;当民族精神衰微不振之时,文化也就处在停滞状态之中。这也是一条文化发展的规律。(《全集》第六卷,第356-357页)
《易传》传统上被看作是孔子所作,因而影响很大,张先生接受现代主流学界的观点,认为《易传》作于战国时代,即便如此,它仍是对孔子学说的发展,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张先生这里也强调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一体性。
1988年12月在《文化体系及其改造》一文中,张先生也说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法国有法兰西精神、美国有美利坚精神、德国有日耳曼精神,等等,“我们也应肯定有一个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一定要发现这种精神、认识这种精神、理解这种精神,然后发扬提高这个精神。我认为这个精神就是《易传》上所讲的两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方面是发挥主动性,积极向上、奋发努力、永远前进、坚强不屈;另一方面是厚德载物。中国自古以来不想向外侵略,修建长城就是个例证。长城是一种防御的设备,不想向外扩张,表现了爱好和平的态度”(《全集》第六卷,第451页)。
总体上看,张先生在1980年代中后期提出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仍特别突显“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爱国精神的重要性,强调要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不屈服任何外来势力;同时,他也提出“厚德载物”之包容、和平精神的重要性,并视之为中华民族的特殊性所在。
三、突出民族精神的主体性、和平性
进入90年代,张先生更加重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民族精神的哲学意义和时代意义,在阐释的重点上也发生一些变化,他更加突出“厚德载物”之和平性特征是中华民族的特殊精神和宝贵品格,同时,在对“自强不息”的诠释上也有些新的富有思想性的提法。
1990年7月30日,张先生在《〈周易〉与传统文化》一文中继续强调《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对塑造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认为这两句话“集中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两条是以孔子的名义发生影响的,在长期历史中,广泛地受到人们的服膺尊崇,激励着广大民众奋发前进、在困难面前决不屈服,同时保持着广阔的胸怀”(《全集》第七卷,第69页)。
1992年1月27日,张先生在《炎黄传说与民族精神》一文第三节“何谓民族精神”中认为,传统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因素,而“严格意义的民族精神专指能促进民族发展的积极传统”,“积极传统即能促进社会发展的传统,消极传统即落后的拖延社会发展的种种思想意识”(《全集》第七卷,第220页)。张先生强调“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千多年,必有其所以能够自立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的思想基础,即是中国文化中的积极传统,即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成为民族精神。一是具有广远的影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二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必然是文化学术中的精粹思想,在历史上曾经具有激励人心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民族精神”(《全集》第七卷,第221页)。
在《炎黄传说与民族精神》第四节专门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张先生说“近几年来,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提出一项见解,认为《周易大传》的两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述。这只是用最简括的词句来表示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这两句话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和丰富的理论含义,这需要加以解释。自强不息的哲学基础是重视人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厚德载物的哲学基础是重视整体的以和为贵的理论”(《全集》第七卷,第221页)。从“以人为本”(主体性)来讲自强,这是张先生之前没有讲过的。接着张先生又展开了更具体的论述,他认为“自强就是在德行、知识、能力各方面不断提高,从而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自强观念包含对于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包含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全集》第七卷,第221页),“儒家强调道义之强,即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坚持原则,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就是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努力上进,决不休止。自强不息的精神亦称为刚健”,“在中国历史上,刚健自强的思想起了激励人心的伟大作用。特别是在国家民族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志士仁人、爱国群众起来进行英勇的斗争,更显出刚健自强思想的光辉”(《全集》第七卷,第222页)。自强不息是积极进取的精神,相比之下,厚德载物是一种“博大宽容的精神”,含有“宽柔以教”的意谓,“厚德载物,即待人接物,要具有宽容、宽柔的态度。既肯定自己的主体性,也承认别人的主体性;既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也要承认别人的人格尊严。在国际关系上,厚德载物的原则表现为和平共处,反对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向来不主张向外进攻,古代建筑的长城,本是一种防御的工程,这也是中国文化中重视和平的表现”(《全集》第七卷,第222页)。个人、民族都有努力保持其主体性的独立和尊严,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还要将心比心,尊重别人的主体性,不能因张扬自己的主体性限制、妨碍乃至打压别人主体性的伸张。张先生此论,与现代西方哲学提倡的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交往理性之说有些类似。贺来认为,“主体性”是哲学中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主体性”观念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进程中产生了十分特殊的作用,对于推动思想解放、观念变革居功至伟(5)。
在《炎黄传说与民族精神》一文,张先生还指出“‘自强不息’的精神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同具有的,并非中国文化的特点。‘厚德载物’的宽容而爱好和平的精神,却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特点”(《全集》第七卷,第223页)。这可以看作是对1986年8月青岛讲话认为只有中国才有兼容并包精神、没有发生宗教战争观点的一种发展。从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厚德载物”、爱好和平的精神非常重要。就此而言,张先生的这一看法是有前瞻性的。当然,这与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也是分不开的。1990年代的中国,政治独立,经济迅猛发展,这与百年前任人宰割的国运已不可同日而语。
1992年4月12日,在《中国文化的光辉前途》中,张先生又说“‘自强不息’,亦称为‘刚健’即奋发向上,坚强不屈,永远前进,决不停止。‘厚德载物’,是宽厚待人,团结群众。‘自强不息’表现了奋斗精神,‘厚德载物’表现了宽容精神。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全集》第七卷,第246页)。1992年5月3日,张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德力、刚柔的论争》一文中“自强不息即是刚健精神,厚德载物即是宽柔精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表现了刚柔的统一”(《全集》第七卷,第253页)。1993年2月9日,张先生在《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一文中说“自强不息涵蕴着主体性的自觉。厚德载物显示着以和为贵的兼容精神”(《全集》第七卷,第329页)。就一个民族而言,自强不息,强调民族的独立与尊严,是爱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厚德载物”,“道并行而不相悖”,体现的包容精神使得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思想主张可以和平相处。1993年7月7日,张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中以“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为中华文化的四项基本观念。显然,后两项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体现,张先生说“在古代哲学中,与刚健自强有密切联系的是关于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和为坚持原则可以牺牲个人生命的思想”“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是刚健自强的最基本的要求”(《全集》第七卷,第382-383页)。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主张就体现了这一点。张先生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家宣扬‘刚健自强’,道家则崇尚‘以柔克刚’,这构成中国文化思想的两个方面。儒家学说的影响还是大于道家的影响,在文化思想中长期占有主导的地位。刚健自强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全集》第七卷,第383页)。
1994年12月4日,张先生在《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的两大基本精神,“一是刚健自强的进取精神,二是以和为贵的宽容精神”(《全集》第七卷,第554页)。张先生在文中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文化安于现状、缺乏西方那种积极进取精神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哲学中,道家固然主张回到自然、反对进取;而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则是主张积极有为的”,《易传》刚健自强的主张“即是能克服一切艰险,这正是积极进取的精神”(《全集》第七卷,第554页)。张先生又说“这种积极进取精神是与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相互近似的。但是中国文化宣扬一种以和为贵的宽容精神,则与西方迥然不同了”(《全集》第七卷,第554页)。这里,张先生也强调了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
1996年2月,张先生在其《全集·自序》中述及生平学术时,最后说“我提出民族精神的问题,认为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屹立于东方,必有其延续不绝的民族精神。我提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周易大传》的两句话来表述,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谓‘自强不息’即是发扬自觉性、坚持前进的精神;所谓‘厚德载物’即是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的精神。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为‘中华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全集》第一卷,第4页)。
张先生生于1909年,2004年辞世,1985年他提出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中华民族核心精神时,已77岁高龄,那么,此后的十多年他一直对此反复宣讲、阐释,在思想文化各界乃至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阐释看起来大同小异,实际上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他的一些讲法也在变化,反映了他对此问题思考的不断深入。同时,从晚年张先生的学术自述来看,他对此非常重视,自觉地将其视为其学术的最后一个重要发明,是对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思想贡献,也是其一生学术情怀的凝结,充分体现了张先生强烈的学术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余论
张先生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这一点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并被普遍认可(6)。张先生讲自强不息,强调其爱国主义精神的激扬,这对我们今天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有影响的。当然,爱国主义更多是乾卦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强调的是民族独立、民族自强,是对民族精神主体性的彰显。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际上也是乾卦精神的体现。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全面来说,讲民族精神,也应包括坤卦的包容精神、和平精神。我们今天讲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结合乾坤两卦的精神来说,连续性是讲生生不息,它与生生日新的创新性,可以归为乾卦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和平性、包容性可以归为坤卦厚德载物的精神,统一性居中可以说是太极大中之道。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辩证统一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恒定的价值观,有永恒性,贯穿过去、现在、未来,民族精神在每一个时代又有着具体的表现,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当下绽放。“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民族精神的很好概况,就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而言,如果继续结合《周易·大象传》来讲,实际上可以加上咸卦“以虚受人”,以及恒卦“立不易方”。乾坤为《周易》上经的头两卦,咸恒为《周易》下经的头两卦,“以虚受人”与“厚德载物”的精神类似,但又有所不同,它更强调虚怀若谷,主动学习汲取别人的长处,与外界发生真切、笃实、畅通、向上的内外感应与信息能量交换;“立不易方”与“自强不息”的精神相呼应,但又有所不同,它更强调自己的原则性、立场性。在新时代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中,《周易·大象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虚受人”“立不易方”,以此作为民族精神的时代新表述,可以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呼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精神力量。
注释
(1)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2)谢幼田:《中国民族精神探析》,《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
(3)迟成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国学大师张岱年的民族精神观的解读》,《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张岱年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5-196页。
(5)参见贺来:《“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6)张先生本人之人格也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写照,陈来指出“张先生一向谦和待人,有求必应,他既是诲人不倦的导师,又是忠厚宽和的长者。‘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是他自己从事学术工作和待人处世的写照”(陈来:《张岱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哲学家》,《燕园问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上一篇】【刘馨宇】孝道真的过时了吗?
【下一篇】贺卡丨中秋节快乐
作者文集更多
- 【翟奎凤】象山研究的新突破 02-11
- 【翟奎凤】张岱年论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及··· 10-04
- 【翟奎凤】儒家中和思想探源 05-21
- 【翟奎凤】“三合然后生”:康有为论孔子··· 05-19
- 【翟奎凤】本天与本心:宋明时期的儒佛··· 03-30
- 【翟奎凤】神化体用论视域下的张载哲学 10-29
- 【杨艳香 翟奎凤】早期“神化”思想的形··· 05-13
- 【翟奎凤】“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源流考论 11-16
- 【翟奎凤】梁漱溟、庞朴与《中国哲学》··· 04-26
- 【翟奎凤】“对越上帝”与儒学的宗教性 12-01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