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素梅】探寻中西方道路的文明逻辑 ——《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简评
由于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关中西方政治文化差异的争议从未停止。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和解读中西方道路的文明逻辑,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其中,分别经历了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辉煌以后,中西方都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政治分裂和文化冲突阶段。然而,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历史和文明历经危···

【潘维】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 ——读潘岳同志文章《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近日读到潘岳同志的奇文,比较五胡入华的三百年和日耳曼各部入主西罗马的三百年。文章说明,这两个类似的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中西后来不同的历史路径和不同的政治结果:一个是族群的分散封建,迄今再未有罗马大一统;另一个是胡汉融为一家、一扫汉末至三国两晋到南朝的颓废,恢复了郡县大一统的勃勃生机。
-1.jpg!cover_160_120)
【吴钩】清明是如何从欢快的节日演变成伤感的扫墓季的?
又到清明时节,正是慎终追远的时刻。不由想起几年前的旧闻:清明节前夕,四川乐山某居民小区挂出横幅,上写“恭祝全体业主节日快乐”;陕西渭南的电信运营商给四星客户群发节日祝福短信:“您好!清明将至,提前祝您节日快乐”。看到祝福语的小区业主与手机用户都很郁闷:清明节不是祭拜先人、寄托哀思的日子么?怎么可以祝“节日快乐”?

【济楚】舌尖上的清明野菜 ——谈寒食、清明诗词中的蔬菜食俗
唐代,寒食节大致演变固定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或前两天),清明节的种种过节习俗,皆为寒食节所包。而寒食节固定到春季,影响非常深远,比如这篇小文将要提到的寒食、清明采食各种山野蔬菜的食俗,只有在春天才有这些舌尖上的口福。

【刘增光,刘林静】2020年儒学研究综述
2020年的儒学研究呈现出多元样态,具体可分疏为五大主题:经学研究的兴盛、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儒家政治哲学的新进展、现代新儒学与儒学研究的新视角,还有一个特殊主题即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儒学界对此人类共同困境的儒学省思。本综述的内容以学界相关专著为主,论文为辅,通过对2020年儒学研究梗概的梳理,呈现儒学研究的最新趋势,···

【陈立胜】刘蕺山“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比配说申辩
本文首先对“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比配说的思想渊源,作了一个细致清晰的思想史谱系梳理。“仁义礼智—元亨利贞—春夏秋冬—爱恭宜别(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者两两相配,这是朱子代表的传统思路。刘蕺山别有心裁地插入了“喜怒哀乐”这一在其看来不可或缺的环节,形成“五位一体”的谱系,以新的方式呈现心性或精神世界原初的时间性和节律性···
-5.jpg!cover_160_120)
【殷慧】宋明理学视野中的修身以礼
礼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原始儒家推崇的六经,皆以礼为本;到宋代礼义的提升,理学话语的展开,最终标志是《四书》辑合成书。无论是理学和心学,均致力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而礼义的突破最终落实为心性修养工夫和家礼的实践。从宋明理学视野中探索的修身之学,一方面就经典世界的创发而言,《四书》文本的相互关联与诠释,从《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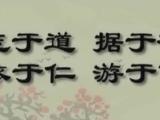
【谢明德】《论语·述而》“游于艺”新解
“游于艺”见于《论语·述而》“志于道”章:“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言简意赅,历来为儒家所重视。艺字的繁体为“藝”,古字作“秇”“蓺”,指种植,如“不能艺黍稷。”(《诗经·鸨羽》)黍稷泛指粮食。从本义引申出知识、技能、艺术等含义。在先秦,艺也称“道艺”。《礼记·少仪》:“问道艺,曰:‘子习于某乎?’‘子善于某乎?’···

【何俊】象山心学中本心与认知格局的关系
陆象山四至十三岁形成的认知格局构成了象山心学的稳定结构,贯彻于他的思想始终。这个格局由相关的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心与宇宙的关系,表征为命题“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另一个是心与事的关系,表征为命题“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全文分三个部分:一是分析象山将矢量性空间转为人化了的空间,从而确立心···

辛丑年清明孔子后裔至圣林祭祖大典举行
岁次辛丑,节序清明,天之朗朗,春意融融。2021年4月4日,曲阜各界孔子后裔代表,以及孔子博物馆、孔子研究院代表等近200人,齐聚孔林,隆重举行辛丑年清明曲阜孔子后裔至圣林祭祖大典。参祭人员身着深色服装,手持祭文和黄菊,在庄重礼乐声中,在礼生引导下,沿孔林神道缓缓前进,经孔林大门、二门、洙水桥、享殿到达孔子墓前,列队···

辛丑年春季祭孔大典在曲阜尼山举行
圣地起雅乐,清明祭先师。4月3日,辛丑年春季祭孔大典在孔子出生地山东曲阜尼山举行,200余名社会各界人士和孔子后裔代表共祭至圣先师孔子。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会副会长、曲阜市政协主席孔令玉主持祭祀大典,曲阜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照辉恭读祭文。参加祭孔的社会各界人士依次向至圣先师孔子像敬献花篮,并行三鞠躬礼。辛丑年···

山西洪洞举办第31届大槐树寻根祭祖大典 传承祭祖习俗守望乡愁
明代,在山西洪洞一颗粗壮的古槐下,官府集结万民,遣送四方。600年后,大槐树移民子孙繁衍遍布中国各地,并辗转迁徙海外。每年祭祖时节,散落在海内外的游子便会向祖籍大槐树聚拢,逐渐成就了洪洞“天下故乡、华人老家”的美誉,回家祭祖缅怀先辈成了各地华人的传统习俗。

学者陕西黄陵探讨黄帝文化与黄帝精神 助力文化传承
祭祀黄帝陵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学术论坛3日在陕西省黄陵县召开,旨在挖掘和弘扬黄帝文化与黄帝精神,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性、民族性、创新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0余名学者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了黄帝与黄帝陵祭祀文化中的思想源流与人文本质,梳理了黄帝陵祭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揭示了···

【张耀南 刘璐瑶】中国哲学构建法、中国哲学史书写法新论
分析甲午以降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构建法、书写法,可清晰发现三款格式之存在:基于“汉学”背景之构建法、书写法;基于“国学”背景之构建法、书写法;基于“华学”背景之构建法、书写法。学者们分别采用三套格式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从“格式学”角度观察,此三款格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常樯】写好中国故事的“儒学篇章”——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发展建设碎思
儒学机构要着力打造“六个平台”——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教育平台,发展学术、服务学者的科研平台,引领风尚、成风化人的传播平台,凝聚智囊、回应关切的智库平台,整合资源、交流对话的互动平台,承上启下、落实政策的组织平台。儒学机构应聚焦学术研究和普及应用两大核心业务。

【罗德】《古易今用——汇通<周易>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与实践》导读
书中所阐发的易学与社会科学合作框架、易学实证研究六步法、三三体例、用《剥》《复》等卦研究儒家乃至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等核心内容,毫不夸张地说均为前无古人的首创,既无先例可循,也无成法可依,真可谓是康老师积数十年功力,持续探究求索、厚积薄发的硕果。

【林桂榛】清明谈传统:寒食、上巳、修禊、夏历、火正、炎帝、灶神等
冬至日起算的十月制夏正前3月尾3日是寒食节,再过一周(6—7日)是上巳祓禊除邪活动,寒食与上巳共连约10日,节气正好,暮春温度阳光正好。

【秦治】有效控制疫情 保障同胞安宁 ——华人心声
每日清晨初醒,点开手机,急切等待《国外疫情最新消息》更新。欣喜昨日新增确诊人数骤减,希望今日继续,然而失望至于一再。肆虐世界的新冠病毒,已蔓延全球一年又半,270多万人失去生命,却依旧看不到好转迹象,怎不令人忧伤。病毒能控制吗?可以,中国经验已经证明,可以在短期内完全控制。然而世界疫情为什么得不到控制呢?

【杨玉婷】朱子《中庸章句》的诠释特点与道统意识
“道统”说在朱子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理解关系到对朱子哲学的整体定位。朱子“道统”说的成熟形态出现在《中庸章句序》,理解《中庸章句》本身有助于我们把握朱子的道统意识。《中庸章句序》指出子思作《中庸》的原因在忧“道学”之不传,提出《中庸》的内容与“道统”的内容一一对应,“道统”与“道学”是统一而非分裂。
-3.jpg!cover_160_120)
【孙向晨】重温《论语》:理解仲尼之光
第一次全文阅读《论语》已是大学一年级,读了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很羞愧没读过《论语》,便囫囵吞枣读了一遍,浮出了一个亲切的孔子形象,一洗连环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留下的阴郁印象。那是个渴求西学的年代,李定生老师曾问,向晨是否继续读中国哲学研究生?内心的理想却是要修数理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