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白银平川忠恒学校和平川职业技术学校举办庚子年祭孔大典暨成人礼仪式
典礼在庄重典雅的古乐声中拉开帷幕,参会领导庄严肃立,神情庄重,与全体师生齐声诵读《论语》经典名句,朗朗书声回荡在中恒上空。祭孔大典仪式后,中恒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带领高三学子及家长走向成才路, 跨过状元桥,迈入成人门,步入成人礼会场,参加下一项庄重盛典——“十八岁成人礼”仪式。

“南孔圣地”衢州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71周年祭祀仪式
纪念孔子诞辰2571周年祭祀仪式在孔氏南宗家庙举行。祭祀活动在庄严、浑厚的《大成乐》中开始,孔子第76世嫡长孙孔令立向孔子像晋香。随后,学生们向孔子像敬献五谷文房四宝。全体参祭人员向孔子像行鞠躬礼,并合唱《大同颂》。受疫情影响,今年的祭祀典礼除了缩短流程,更是首次在网络平台举行“云祭祀”。

【阿拉姆·阿尔帕特】西方哲学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不光是黑格尔或卢梭是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深藏在其辩证哲学的结构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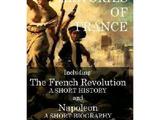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没有压舱石的航行
法国大革命及其现代政治实验对当今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狐狸与刺猬:通才的过去与未来 ——《通才的文化史:从达芬奇···
当今可以找到的西方哲学经典的最古老文献之一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c.535–c.475 BC)的手稿残片,我们在其中读到“博学多识(polymathiē)并不能让我们的理解能力有多大提高。”
-6.jpg!cover_160_120)
兰州交大读《论语》作业系列丨【宋瑶瑶】积累点滴,汇聚成自己的江海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开篇的这几句话耳熟能详。学习《论语》从小就开始了,但对于《论语》的深刻学习,在我踏入兰州交通大学校门后才真正开始。

兰州交大读《论语》作业系列丨【赵楠楠】青衿之志,诗书芳华
最近在阅读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著作《为什么读经典》,书中这样写道: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对于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从小便耳濡目染,书中的经典句子也能背诵一二,但这次重读《论语》却有不一样的收获与感悟。

【东方朔】荀子伦理学的理论特色——从“国家理由”的视角说起
在荀子,国家是以“圣王”和“礼义”来表现的,礼义所具有的止争去乱的功能以及规范行为的性质,其实质是以“国家理由”的形式出现的;国家之所以必须并且必然,乃是因为其深深地根植于人的性恶的天性之中,而荀子所说的人性的“恶”,并不是在特定的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恶,而应当被理解为政治意义上的“偏险悖乱”。
.jpg!cover_160_120)
【杨赛】颛顼与喾的礼乐文明
颛顼乐和喾乐是黄帝乐传承中重要的一环。颛顼效法黄帝制作《承云》,《云门》以视觉图腾为主,《承云》则以听觉图腾为主。颛顼效法黄帝《咸池》制作《六茎》,宣扬普施恩泽的执政理念,以争取民意,巩固统治基础。

各界人士长沙公祭王船山
17日,庚子(2020)公祭王船山仪式暨纪念郭嵩焘开创公祭王船山新传统150周年雅集活动在位于长沙的湖南自修大学旧址(原为船山学社旧址)举行,来自北京、南京等地的各界人士参加。

【王琦 朱汉民】屈子书院:爱国忧民 修远求索
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是为了纪念与弘扬屈原爱国主义精神而建立的祭祀、讲学与培养人才的场所,创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又名汨罗书院、清烈书院、屈原书院等。

【韩星】《论语》仁学体系新诠
孔子思想主体是仁学。“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即仁不仅是人之为人的底线,也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仁”,“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核心、包诸德、合天人、贯内外,通透于其个体生命的成长之中,造就了至圣的人格境界。孔子“仁学”为传统儒学奠定了基本规模和诠释方向,对于今天重建新儒学思想体系具有正本清源、返本···

【任锋】修齐治平,才是大学——在2020-2021学年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孔子则讲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次第,修齐治平,才是大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学问扎根在中国大地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政治学是经世致用的大学问,通人通儒的“通”就在调动一切知识资源来追求共同体的公共福祉。希望大家在人大有更深的体会。

“文明竞合与秩序重整:钱穆逝世三十年后的新世界” 学术研讨会侧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本次研讨会正值庚子巨变之年,世界局势云谲波诡,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大半年亦未见消歇。如何在沧海横流中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在现代当下实现中国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乃至个人如何像钱先生一样在时代的急流中立定脚跟,都是我华夏有识之士绕不开的难题。

【王心竹】浅论先秦法家对儒家德治的批评——以商鞅、韩非为例
法家明确反对儒家的德治,将其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同时,与儒家对君主提出道德要求相反,认为君主之德与社会治乱没有关系。而法家之所以重法,反对德治,在于他们认为人在本性上是自私和功利的,必须以强制性的法加以规制。法家虽然反对德治,但并不完全是非道德主义。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与创新专题研讨会暨辅仁读书会十周年纪念会成功举办
2020年10月11日18:30,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辅仁读书会于主楼A803成功举办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与创新专题研讨会暨辅仁读书会十周年纪念会。

“泰州学派学术高峰论坛”征文启事
泰州学派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派以地名,地以派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给后世留下了追求真理、开拓创新、心怀天下、关注民生等丰富的思想遗产,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泰州具有较高识别度的城市文化名片。

2020全球祭孔图集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为了集中展示全球各地祭孔活动,儒家网特别编选年度图集,以飨读者。

甘肃武威文庙隆重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71年释奠礼
2020年9月25日上午10点,庚子年武威纪念孔子诞辰2571年释奠礼,在武威文庙隆重举行。220名居住在武威、金昌、兰州的孔子后裔参加祭孔大典。

何益鑫著《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出版暨后记
本书是对《性自命出》的文本与思想的专门研究。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从思想史的角度,阐明《性自命出》的“性情-心术论”思想,乃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发端;第二部分为“章句”,以简要的方式注释文本、提示章旨、勾勒行文思路和文本结构,为后续的探讨提供一个简明可用的版本;第三部分为“讲疏”,在综合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