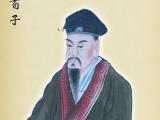
【姚海涛】荀子对数术的系统批判 ——以占卜、相术、厌劾祠禳为中心
荀子对数术虽没有专门立论批评,但检视《荀子》一书,可抽绎出其对数术传统的系统批判。

【吕庙军 林桂榛等】拿经验主义科学主义套荀子是唐吉诃德与开玩笑吗?
孟书以人有天赋仁义等而本有伦德以言性善,荀书以人有天生情欲等而多生争乱以言性恶(开篇实本是驳孟以论性不善而已),白纸黑字,板上桩钉!

【强中华、林桂榛等】关于荀子《性恶》“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的讨论
“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辨]知[智]”,性质即性材即材性,材性有美恶,即使材性美良,即使心辨[心识]智明……该处完整全句意思是:即使材性良好、心识上乘,得交接正面的贤良而靡积进步,反之交接不贤良而靡积退步堕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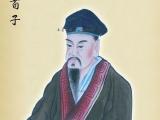
【周启荣】礼法儒家:荀子的“群居和一”社会论与“性恶”论的关系 ——兼论儒学发展的···
本文主旨有三个:第一,从历史文字学来论证荀子性恶论中“恶”的各种用法,並在这个基础之上重新分析“性恶”的“恶”字应指“静态厌恶”,而不是“动态作恶”的涵义;第二,分析性恶论在荀子儒学礼法系统中与他的“群居和一”社会论的逻辑关系。第三,荀子发展孔子礼法思想的重要性在清代随着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而得到承认并推广,通过对戴震与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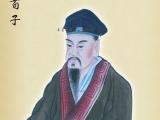
【纪洪涛】荀子“天论”中的人学观
荀子是战国末期集儒学大成的思想家。《荀子》之“天论篇”集中论述了荀子对天的认识。细究文本,“天论篇”之表象在于言天,而其旨归却在论人,荀子在天与人对勘的结构中以天论人,阐述了深刻的人学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辩证天人观。

【姚海涛】文化批判与理论熔铸——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中的作用研究
齐鲁文化合流分为三个阶段。在合流的后两个阶段,荀子主要发挥了文化批判与理论熔铸的巨大作用。 他从解构与重构的道统、传经与弘道的学统、建构与影响“礼义之统”政统三个维度对儒家“三统”的形成、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齐鲁文化合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纪洪涛】荀子“天论”中的人学观
荀子是战国末期集儒学大成的思想家。《荀子》之“天论篇”集中论述了荀子对天的认识。细究文本,“天论篇”之表象在于言天,而其旨归却在论人,荀子在天与人对勘的结构中以天论人,阐述了深刻的人学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辩证天人观。

【干春松】荀子和李斯对于“历史时刻”的认识——评潘岳《战国与希腊》一文
我们现在正经历新的“历史时刻”,这个时刻即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我们突破“小道”“小力”,而追求人类之公共福祉。荀子相信圣人可学而致,我们每一次对于自己的局限性的突破,都是对“天下主义”的接近。而如果沉沦于依赖于术势的统治术,则是“坐井观天”的自缚之道。

【姚海涛】荀子意义之散思——由潘岳《战国与希腊》谈起
一个以往被忽视的荀子出场对于思想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荀子所处的战国末期距今也已2200多年,与21世纪之新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当下人类所处的内外环境、所遭遇的问题、对于未来的遐想与憧憬,荀子有无意义,在何种程度上还具有意义,又有何种意义?这些问题的解答只有回到荀子本身才能找到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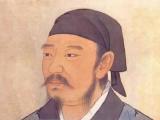
【方旭东】“天学”视野中的荀子——利玛窦对《王制篇》物种分类说的改造
《荀子·王制篇》关于物种分类的一段话,被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引来支持其批判宋明理学万物一体说。仔细比照,可以发现,利玛窦对荀子原文做了一种改造,诸如:将“气”写作“形”,将“水火”写成“金石”,将“义”写成“灵才”,等等。这种改造典型地反映了中西思维的差异,为我们了解荀子在西学尤其是天主教神学视野中的镜像提供了一个典型范本。
-7.jpg!cover_160_120)
【东方朔】荀子的“知明而行无过 ”
荀子虽然主张人的本性是恶的,但是,他对一个人能够成为有道德的君子乃至圣人充满了信心。他坚持“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一个人只要广博地学习礼义,且能够以礼义反省修身,则可以达到“知明而行无过”,最终成为有道德的人。
-12.jpg!cover_160_120)
【姚海涛】天生人成与礼术合一——荀子养生之道诠论
天生人成与礼术合一构成了荀子养生思想的两大支柱。其中,天生人成是荀子养生之道的基石,指向了其养生的丰富层面——身、心、性、情、欲。礼术合一是荀子养生之道的具体下贯与落实,指向了养生的具体理论。具体言之,礼术合一包含了礼以养体、礼以别异、礼以制欲的中和养生之道以及中和以养气、床笫之私有度、莫善于诚、虚壹而静等诸多···

【余治平】“荀子入秦”:何以成为一次文化事件?——儒者直面法家治理的精神体验与思···
荀子最先从强秦的一派繁荣中看到了其灭亡的迹象,而“唱衰”秦国,矮化秦政。而随后不久强秦帝国的轰然倒塌、关于儒法孰优孰劣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实践,则更说明“荀子入秦”堪称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

【东方朔】“欲多而物寡”则争——荀子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和出发点
随着简帛文献尤其是郭店楚简和上博竹书的问世而逐渐为学界所重视。一些儒学史著述,也开始改变过去的“孔-孟-荀”的先秦儒学三段论叙述,将子思纳入儒学史。为厘清有关问题,本文希望能够在前人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考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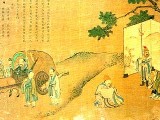
【刘丰】从《儒行》到《儒效》:先秦儒学的发展与转折
荀子严厉地批评了俗儒、贱儒、小儒,同时提出了大儒理想。相对于《儒行》篇而言,《儒效》篇对儒者的定位与理解已经比《儒行》篇有了极大的提升与飞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扭转了儒学发展的路径,即更加重视儒学中的政治品性。这一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汉代儒学的发展。
-10.jpg!cover_160_120)
【李承贵】荀子的教化思想
本讲分四个问题,一是荀子提出教化的根据;二是荀子提出的教化方法;三是荀子对教化特点的认识;四是荀子教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思考。

【杨国荣】荀子论修身和成人
从孔子开始,儒学便十分注重修身,而修身过程又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儒学中的重要人物,荀子也延续了将修身与“学”相联系的传统。
-9.jpg!cover_160_120)
【白奚】荀子与稷下诸子
学术界一般认为,荀子集先秦学术思想之大成,他的思想是先秦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但是,荀子的思想为什么能够成为最高峰?

【东方朔】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以权力来源为中心
有关荀子“政治正当性”的主张,已经有许多有益的探讨。站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政治正当性”所预认的观念前提在于民众的自我意志的自由和自决,舍此,则任何权力的“正当”或“不正当”皆无从谈起。正是从此前提出发,荀子在权力来源的问题上并不曾追问权力本身的正当性问题,而更多的是在意统治者统治权力在效果上的合理性问题。造成此···
-168.jpg!cover_160_120)
【王正】重思荀子的“大清明”
学界对荀子的“大清明”观念一直研究不够,但此观念实蕴含着荀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由认知之心是否可以通于道德和政治。事实上,荀子认为:通过“大清明”的认知之心,人可以认识到至善——道,并以之来对治自身心性和各种现实中的恶,进而使自身和现实都达到善。可见,如果我们转换港台新儒家从孟子出发的心性论样式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