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凌杰】何以为宾:试论经学视域下“宾礼”概念的构建
经学中的“宾礼”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概念,《周礼·大宗伯》只有“朝、宗、觐、遇、会、同、问、视”八种极为简略的定义,经过郑玄、熊安生、孔颖达等人的注疏,宾礼从诸侯朝天子泛化为天子、诸侯、卿、士等贵族之间的相见聘问礼,也指代不臣服于天子的特殊群体之礼。现今学界将“宾”“客”“宾礼”“客礼”视为具有清晰内涵与外延的稳定性概念···

【陈佩辉】“美德经济学”与“哥白尼革命”:陈焕章儒家经济学的性质与定位
陈焕章认为缺乏道德根基的放任主义只给强者带来利益,必致社会分裂和崩溃。为了阻止经济的去道德化,陈焕章认为社会经济秩序应该建立在道德和经济双重动机之上,并建构了以美德为中心的儒家经济学。

唐文明 著《极高明与道中庸:补正沃格林对中国文明的秩序哲学分析》出版暨导论
本书聚焦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尤其是《天下时代》,试图回答“沃格林不同时期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文明”和“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沃格林的中国文明研究”这两个关键问题,在梳理其秩序哲学全貌并且高度认同其秩序哲学理路的基础上,补充沃格林原有分析的不充分性,修正不正确性,进而回应中国文明如何通过持续不断地向西方文明进行深度学习,···

【段重阳】存在论、根据律与体用论的形而上学
在中国哲学中,物并未基于“相—是”得到把握,“用”成为中国哲学对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根据的物之“如何”。从“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规定性,即物之“体”,而这种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时,更指向了对存在者之整体及其根据的把握,因而通过体用论展开的对物之“如何”的追问表明自身为以“天德”或者“天理”为根据展开的形而上学体系。

【黄玉顺】情感儒学: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一个范例——蒙培元哲学思想研究
蒙培元在其数十年的研究工作中,不仅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力重新梳理了儒家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而且以其深刻的思想洞见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情感哲学”(学界称为“情感儒学”),包括其中涵摄的次级理论“心灵哲学”和“生态儒学”。

【张玉晶】重思钱穆与张君劢中国古代政制之辩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否为专制的问题从未缺乏过探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新制,是现代新儒家共同关注的话题。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正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要明确“专制”概念的中西差异,而不是一定贴上“专制”抑或“非专制”的标签,这才是···

【蔡杰】《儒行》的超越维度:儒家群体的建设与追求
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

【张晨】血缘、秩序与天道:公羊家视野下的家国公私问题
公羊学家通过对为父绝母当否、为国诛兄义否、为父灭国可否三事的讨论,提示出一条新的路径:重视秩序建构,申明公高于私,在严辨公私之分的同时兼顾亲亲之恩,既避免了因人情泛滥而导致的以私灭公之弊,又规避了因过伤人情而流于暴政之患。

【李竞恒】朝鲜《燕行录》文献中的“汉衣冠”与头发
在朝鲜人笔下,汉人会为衣冠头发而哭泣,有人因见衣冠而提出想逃往朝鲜,还有人通过偷穿戏服、家藏旧衣或朝鲜冠服来体验“汉衣冠”。甚至满洲人,也对“汉衣冠”表达出欣赏与向往,其中或有夸张与想象。到晚清,朝鲜人则配合清朝防范太平天国可能利用“朝鲜服色”。衣冠头发之悲,则指向了明治维新后改穿西装的日本。

【谷继明】清中期以来的乾元太极论
《易传》中的乾元与坤元到底是一或二,以及太极与乾元、坤元的关系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易学诠释史和哲学史的发展。清代汉学兴起以后,不少易学家又在汉代易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思路。惠栋以“元”解释太极,反对以“无”来解释太极。张惠言从画卦的角度以为乾元即是画卦的一卦始基,也即太极,并且直接断定“坤无元”,此说为姚配中···

【高海波】生生与孝弟慈——明儒罗近溪的仁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明儒罗近溪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及工夫追求,建立了一个以易学的生生观念为形上基础,以“不学不虑”“百姓日用”为工夫判准,以“赤子之心”和孝弟慈为核心的仁学体系。这一体系十字打开,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是儒家仁学本体化、社会化在明代最成功的范例。系统阐发罗近溪的仁学思想,对于建构当代的新仁学,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吴飞】仁之实与仁之端——《孟子》仁说发微
孟子对仁之实的讨论,是在文质论的架构中展开的,需要加以节文,而对仁之端则需要扩充。这两个方面并不相同,是交错展开的。作为仁之实的事亲即亲亲,根本上来自生生,却不等于自然的生生,而是因对生之反思性确认而产生的德性,这与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是非常不同的。由消极的恻隐之心来理解人性,是孟子人性论中非常独到的人性论···

【任锋】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化合?——从钱穆礼教论省察亨廷顿命题的困境与出路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论,能否提出基于中华文明的系统性、批判性思考在新时代愈发显示出切要性。钱穆从宗教学切入中外文明比较,特别注重阐发与心教相为表里的礼教论,将其置于文明类型说的立国政教视野中加以鉴别,预示出亨廷顿命题的一个替代性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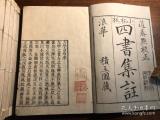
【江求流】《四书》的成立与儒家经学的更新
基于《四书》所形成的新经学必然是一种儒家式的心性之学,但这种儒家心学又自觉地建立在《四书》等经典文本之上,而没有试图像禅宗或陆王心学那样废除经学、解构经学,而是更新、重建经学。另一方面,这一新经学虽然以解决治心与治世的贯通为总体指向,从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哲学色彩,这一新经学并不仅仅只向政治主体开放,而是向一切主···

【陈赟】六经成立与中华文明的精神奠基
“经”的常道性格的确立并不意味对“史”的贬抑或泯除,相反,“经”在“史”中展开并充实自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故事,不再是周期性的、可重复性的、可以通过仪式行为不断被展演的非历史性神话或寓言,而是作为承载常道之历史性展开的人和事;他们一旦被纳入六经,纳入圣人之统,就构成中华文明的活着的礼法。

【苟东锋】从“尊贤”到“知贤”——论子思的“合外内之道”
鲁穆公时代,一些心系鲁国之士在比较齐鲁两国发展道路及政治现状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到了“尊贤”的重要性,进而导向两种学说:墨子贯彻了彻底“尊贤”的原则,明确打出“尚贤”的旗帜,由此发展出一套功利之学;子思则逼问“尊贤”何以可能,深入探索“知贤”的理论问题,藉此将儒学引向了一种心性之学

【曾振宇】从“仁者安仁”到“仁以为己任”:儒家仁学从孔子到曾子的演进
孔子仁学重心不在于从认识论维度界说“仁是什么”,也不单纯在道德层面表述“应该”,而是更多地关注身心合一。这种审美境界的仁学,对外在客观必然性已有所超越,其中蕴含自由与自由意志色彩。弟子曾子从两个层面深化孔子仁学:其一,从气论论证“人性仁”;其二,从工夫论的视域诠释仁,将仁学“下贯”于经验世界劈柴、挑水生活之中,形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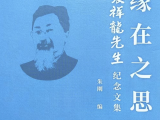
《缘在之思——张祥龙先生纪念文集》出版暨编后记
张祥龙先生逝世后,亲人悲恸,学林震惊。哀伤之情不能自已,许多亲朋故旧、学界友人写了大量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和挽诗挽联。为了不辜负亲友们对张祥龙先生的深情怀念,张祥龙先生弟子朱刚受师母张德嘉女士委托,将大多数纪念文章和挽诗挽联汇编为《缘在之思——张祥龙先生纪念文集》一书,目前该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姚洋:把经济学作为一项 “志业”,而不仅仅是谋生 “职业”
最近几年,由于世界局势变化,姚洋想发展出一套对应理论,开始对儒家政治哲学产生兴趣。尽管心中有正义冲动和经世济民抱负,但作为学者,还是应该做社会的旁观者,因为社会分工要求学者公正、冷静和深入分析社会。不过,重视旁观和分析并不代表虚伪的价值中立,他认为值得警醒的是,经济学界一些人滥用经济理性,忽视社会的其他价值。

【胡兆东】魏晋玄学家是如何看待孔子的
玄学家们塑造了孔子的三种形象:兼爱济物的君子、体无应物的圣人、游外冥内的至人。虽然形象各异,但孔子在玄学家的笔下都不是被排斥、鞭挞的对象,而是境界高妙、爱民济物的超然存在,是隐藏在世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