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益鑫】《大学》首句与周文政治理想
《大学》首句乃是全篇的宗旨所在。它以《周书》等所见的周文理想政治之传统为依据,提炼出儒学最高的实践理想。就其古义而言,“明明德”是在政治领域中显明其光明之德,亦即行明德之政。明德之政,除了恤民怀柔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选贤任能。行明德之政,即亲民、安民的过程。
-39.jpg!cover_160_120)
【李文文】《大学》中的财富观
儒家歌颂人类的创造之力,将人视为与天地之共创者,以创造为使命。创造财富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贫穷往往意味着苦难。任何理想社会形态的建构都不能背离财富的支撑,如何面对财富,是关乎社会、人生的大课题。如众周知,《大学》作为儒家四书之一,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面对财富这样的大课题,提出“德者,本也;财者···

【高希中】《大学》“格物”释义辨析
“格物”出自《大学》,《大学》本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至宋代时,朱熹将其从《礼记》中单独抽出,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儒家思想乃至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尔雅台】大学贯解(中下)
提撕操存是涵养功夫。才操存涵养则此心便在。

【尔雅台】大学贯解(中上)
天命性于心,心作统率,其义有三:一曰虚灵不昧,二曰出令而应万事,三曰道之工宰(荀子语)。

【尔雅台】大学贯解(上)
周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于是孔子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纲领八条目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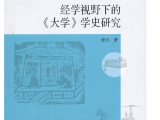
【韩星】经学视野下《大学》诠释史的学术回顾与问题反思 ——读张兴《经学视野下的···
张兴博士的《经学视野下的〈大学〉学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在他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是在经学的视野下对汉代以来《大学》诠释学术史上几个重要阶段、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所作的学术史梳理,初步形成了《大学》学史研究的框架。

【肖新平】《大学》中的德治理念
《大学》《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个单篇,西汉武帝时收录于《小戴礼记》,后来简称《礼记》。宋代理学兴盛有了“四书”,并且出现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到了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确立科举考试第一场从四书内出题并结合朱熹的《章句》《集注》进行论述,后这一制度又被明代、清代继承,继而演变为八股取士,于是四书成为···

陈立胜教授做客人文讲坛·儒家文化研习社:《大学》是如何成为儒家经典的?
近日,中山大学陈立胜教授做客人文讲坛·儒家文化研习社,梳理了《大学》经过韩愈、李翱、二程和朱子的不断表彰而上升为四书之首的过程,细数了围绕《大学章句》《古本大学》《石经大学》以及《大学》“圣经”地位所产生的争执,阐释了《大学》“全体大用”言说架构在儒学与佛道“对话”中的重要性,揭示了《大学》文本对宋明理学宗旨演进的···

【李旭】《书》《诗》政教传统下的 《大学》义理纲维
根据《康诰》之政教理念,观照《大学》首句"明明德"语,可见其蕴含双重"明"义,实际上对应于"天命在周"这一终极状态;继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盖依循周公守成之教,呈现"承天命→保民→敬德"的推本逻辑。八条目"明明德于天下"至"格物"之论,乃承接这一推本逻辑而来;后续格致至治平之序,复由本及末,正面拓展出一条明德开显之路

【陈来】《大学》的作者、文本争论与思想诠释
从今天来看,《大学》陈述的思想里面,应该最被突出的是它所讲的以忠恕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大学》的明德思想和“明明德”的说法是我们今天强调提倡明德论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我们今天要更好的结合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对明德的论述,进一步阐述阐扬《大学》里面的明德说法,让它为我们今天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张文智】《周易》哲学视野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兼论“内圣开出新外王”说之相关问题
《周易》哲学可以为“内圣外王”说提供本体生成论依据。牟宗三先生的“内圣开出新外王”基于其“良知的自我坎陷”说,其所说的“返本”没有真正返回到道之本体,故不可能开出真正的“新外王”。必须把《大学》《中庸》及《周易》贯通起来,才能把握“内圣外王”说的全部内涵。

【杨朝明 李文文】《大学》中的那个“大”
《大学》共1700余字,论字数,在儒家“四书”中是最小的一部,然而,正如它名字中的“大”所昭示的,它其实是一部非同寻常的大书,其中包含了中国的大思维、大格局、大学问。

【杨海文】为修身而正心:《大学》传七章的思想史阐释
《大学》传七章以72个字的短小篇幅,通过设问、病症、后果、劝谕四个层次,试图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如何为修身而正心。学术界迄今缺少对于这一章的专门研究,思想史阐释显得极有必要。

【王琦 朱汉民】论宋代儒家新帝学的兴起
宋代以文治国方略的确定与经筵制度的定型,促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重权术与治术的儒家新帝学的兴起。士大夫与帝王在以经筵为平台、以经典为媒介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学,以《大学》为框架,以君德成就为根本,以尧舜圣王为榜样,指导帝王为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与理论体系,以此确保儒家王道理想的实现与社会政治···

【梁涛】以《大学》理解儒学的意义及局限 ——兼论统合孟荀
儒学包含了成己安人、“为政以德”与推己及人、“为国以礼”两个方面,前者由道德而政治,可称为孔孟之道,后者则由政治而道德,可概括为孔荀之制。

【石立善】《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经典地位的下降
历来研究《大学》与《中庸》,多关注这两篇脱离《礼记》作爲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却无人注意《大学》、《中庸》在明清时代重返《礼记》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影响甚大,在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也非同寻常。
-24.jpg!cover_160_120)
【孔祥安】《大学》之道及其三个向度
《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儒者的特别注意和关注。从唐朝时期韩愈、李翱推崇《大学》《中庸》以来,它才逐渐被一些儒者所重视。迨至宋朝著名的理学家、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将其编入“四书”,便与《论语》《孟子》《中庸》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且居“四书”之首,确立了其在儒家经学史上···

【王琦】朱熹帝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以《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从《壬午应诏封事》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王之学,到《癸末垂拱奏劄》《庚子应诏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拟上封事》,朱熹的帝学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发展与定型的过程,其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通过讲明《大学》之道以正君心立纪纲,规范帝王的德性修养与政治治理,从而贯通学术与政治,成就君···
-1.jpg!cover_160_120)
【申淑华】《大学》研究现状及未来研究旨向
《大学》自宋儒尊信表彰以来,解说纷纭,莫衷一是。学界对《大学》研究的分歧主要围绕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篇名含义等问题展开。目前学界对《大学》的研究呈现两种态势:一是围绕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或某个历史时期对《大学》展开的研究;二是将对《大学》的研究置于四书学之中,缺乏像对《论语》《孟子》那样所进行的学术史的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