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凯】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

【卜松山】跨文化对话如何进行?
围绕“跨文化对话”,我在本文中提出方法论层面的十点思考,涉及如何进行跨文化对话,以及跨文化对话的影响参数、局限性和有利条件。

【谷继明】惠栋的性情论及其在清代哲学中的定位
惠栋通过文献学考辨,指出《文言传》“利贞者性情也”的“性情也”本当作“情性也”,以此批评王弼、程颐等有“性善情恶”之嫌的“性其情”说。与此相对,惠栋斟酌《参同契》等古义,提出“推情合性”说,即情之发自然合于性,以与《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发明。

【专访】朱永新:大学书院制的实践路径与方法
近日,为总结和反思近十年大学书院制的经验与不足,推进古代书院传统与当代大学教育改革发展相融合,在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系列活动中,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人文高等研究院、凤凰网特策划组织“守正创新:书院传统与新时代大学教育”高峰论坛。特邀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先生主讲高峰论···

【蒙曼】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中华诗歌怎样塑造了中国人共同的···
1900年,敦煌藏经石室打开。就像藏有绝世武功秘笈的暗室被开启一样,无数珍贵的文献重见天日,其中包括大量的唐代诗歌写本。这里不乏鼎鼎大名的诗人的作品,包括刘希夷、陈子昂、孟浩然、李白、高适、岑参、白居易,等等。

【张传海】智的直觉何以可能?——以康德、牟宗三、朱子为中心的考察
在朱子那里,性理与形气作为知觉的不同来源,皆具有物自身的意义,但性理具有更加根本的地位。性理以其绝对创生性,自行进入知觉而内在于知觉,所以道心即是智的直觉;也内在于形气,所以人心也以性理为本源。由此,道心以性理为其积极内容,达成了对人心的肯定与成就。

【王宇】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
朱熹进而提出“嫡孙承重”的礼制安排,要求宁宗为孝宗服三年之丧,从而跳过太上皇光宗,强化了宁宗政权的正当性来自孝宗而非光宗这一立场,从而彻底肃清光宗的负面政治影响,树立孝宗这一道德典范(为高宗服三年之丧)。总之,朱熹推出宁宗“嫡孙承重”的礼制方案,可以视为道学集团为了在即将展开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主动权而采取的先发制人···

【胡振夏】阳明知行合一基于「知」的论述——从「知孝悌」的诠释来看
阳明基于「知孝悌」这类论述来阐释知行合一的思想,「知孝悌」意指「孝悌」的内涵自然灵明,意即某一流行发生自行展现为呈示该内涵的施展。「知」理解为灵明,「行」指呈现该内涵的灵明流行,两者是从不同侧重对此流行发生的论述,而「知孝悌」便是展现这一思想的论述方式。

【刘悦笛】良知与良觉,性觉与心觉——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儒佛之辨
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

【蔡家和】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心物关系
心与物的关系,一方面真有主观原则的心,另一方面有客观的物,都是真实的存在,而心能知物,知物所以然之理。心能穷理,格物是不能离于物,面对物而穷其理,而穷理的主词是人,是人心,穷理后则能有知,此为致知,则人心之知做积累工作,做到豁然贯通。

【颜炳罡】轴心文明与齐鲁文化的多重意蕴
齐鲁文化有四重意义:其一,轴心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西周到秦统一这一时期齐国与鲁国的文化;其二,经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主要指秦汉到魏晋流行的齐学与鲁学;其三,行政区位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山东文化;其四,思想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始于轴心时代,以德为先,以修、齐、治、平为目的,主张礼法并治的治理体系与生活方式。

【何益鑫】论孔子的人性观及其展开形态
人性是有个体差异的(差别一般不大,也不排除极端情况);性中有善的成分,也有不善的成分,主要通过好恶表达出来;人生的现实,取决于后天的养成,一个重要方式是顺着性之好恶而来的引导和塑成。要之,孔子持有的应是一种形式的“性有善有恶论”。七十子后学的“性有善有恶”及“养性”说,就是孔子人性观的明确化和展开形态。

【任蜜林】“《易》为之原”与“天人之道”——刘歆易学思想新论
在“《易》为之原”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对“五经”的顺序作了调整,把《周易》置于首位。刘歆提出“《易》为之原”的思想,与其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有关。在“天人之道”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创作了“三统历”,其目的是以天统指导人统。刘歆创建的以“三统历”为核心的系统,不仅体现了其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

【苏杭】易简与体用——以“易简”诠释的思想变迁为中心
汉唐注家往往将“易”“简”解为“无为之道”,并将其视作对乾坤体性的摹状;而朱子认为“易”“简”更偏向“动用”一端。从《系辞》本义来看,“易”“简”分说不能简单地从“静体”和“动用”的角度来理解,“易”指乾以动为本,但同时又兼虚静;“简”指坤以虚静为本,并兼动实。而“易简”合说又是对生生道体的摹状。《易纬·乾凿度》提出了“虚无感动”说,易···

【李明书】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专注”与“动机移位”
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张新民】过化与施教——王阳明的讲学活动与黔中王门的崛起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针对大、小两种传统受众的不同,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学活动,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众,化导移易了民间社会风俗,也培养了不少科考读书士子,构成了王学地域学派的中坚。贵州既是阳明的“过化”之地,也是他的“施教”之区。而黔中王门学者受阳明心学思想的沾溉,主动践行“知行合一”实践哲学精义,不仅人才群体济济兴···

【黄德宽】《说文解字》何以成文字学千古经典
文字的创造和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只有汉字从创造之日起延续使用至今未曾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汉字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也是传承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典文明,之所以能完好地传承,汉字发挥了无以替代的巨大作用。不仅汉字历史悠久,对汉···

【马士彪】儒家境界体验中的抽象置定与具体表现——以牟宗三对阳明与二溪的诠释为中心
儒家的实践不仅关涉到工夫实践中的身心状态转换,亦关涉本体呈现后的境界体验。目前学界对两者的研究,往往借助“逆觉体证”与“冥契体验”的解释框架,但两者都未触及理学家境界体验表达中的本体状态转换问题,牟宗三透过“超越的分解”与“辩证的综合”方法对阳明与二溪境界体验表达所蕴含的深层义理结构——“抽象置定”与“具体表现”——的揭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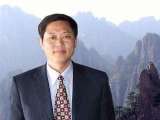
【林忠军】儒家易学传承、创新和重建及其现实意义——以《易传》为视角
今天易学研究当从易学经典出发,借助于传统的象数训诂兼义理等方法,重新解读易学经典和已有研究成果,以客观再现易学文本固有之意为导向。然后在此基础上,以道器关系为出发点,借鉴当代哲学思维方法和学术文化成果及科技知识,促进传统的易学与现代知识深度融合,重建贯通古今中外思想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新的易学文化···

【解扬】古典公共性的生成:乡约的合理性与明代思想史上的和会趋势
从吕柟、罗汝芳等所行著名乡约可见,明代乡约在与《大诰》《明会典》结合并落实于地方自治之后,与明太祖圣谕六条融合,针对社会全体,提供了覆盖面更广的道德训练。这对明代国家而言,在地方自治层面具有特殊的价值。明代的乡约虽然延续了北宋《蓝田吕氏乡约》的传统,但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其存在具有更充分的合理性,也符合当时思想···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