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海军 著《独尊儒术前夕的思想争锋:汉初“前经学时代”研究》出版暨余论
自汉朝建立至儒学独尊,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颇具独立性的阶段。汉初延续战国末期诸子百家的传统,有着长达七十余年的思想争锋局面。

【曾海军】由“数人之齿而以为富”的批评见儒墨之别
墨子虽称尧舜,但讽刺起孔子来也毫不留情,挖苦孔子的博学不过“数人之齿而以为富”,显得比较过分。更过分的是《墨子·非儒下》篇,对孔子的各种批判乃至人身攻击。

【曾海军】汉初儒道间的三次交锋
曹参从“未知所定”到定黄老之术,道家虽说赢得毫无悬念,一切都显得云淡风轻,但就学问本身的思想主张而言,具体表现为勿扰狱与勿扰市这两方面,儒家也一向反对不教而诛和与民争利,相比之下并无特别出彩的地方。

【曾海军】“仓廪实则知礼节”有什么道理吗?
《管子》一书中多次出现的“仓廪实则知礼节”,后世典籍多有引用,亦为现代人所熟知,堪称流传广远的经典名言。

【曾海军】汉初儒道间的三次交锋
窦太后受黄老道家的影响,除了守住类似于清净无为这种教义,对于王臧和赵绾积极推动各种典章制度的建设,缺乏基本的认知,一律当作“此欲复为新垣平邪”处理,运用皇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是儒家在独尊前夕的最后一次曲折,也是黄老道家的势力最后的激烈挣扎。

【曾海军】“道”何以不远?——“道不远人”的时空演绎
道与人不相远,或道与人合一,不是空间距离上的远近,也不是当下洞见这种意义上的合一。只有置于一个时间的跨度上,比如当下、日月、三月之类,这才会由于某种偏离而产生或远或近的现象。颜子“三月不违仁”,实乃日复一日“克己复礼”之功。

【曾海军】“人能弘道”辨正
无论在社会历史层面,抑或整个自然科学领域,人无从弘其道,唯一能做的就是知之,人能弘道变成人能知道。儒家属于“人能弘道”的传统,首先意味着立足此世、重视躬行之学,而区别于其他各种以道弘人的文化,主要追求彼岸世界的圆满。

【曾海军】“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形上之辨
“有生于无”的形上之思,孔颖达在由韩康伯开辟的道路上陷入困境。“无”本身必须得到改造,才可能找到出路,这正是周子所论“无极而太极”的精妙之处。现代哲学凭借其思问方式,对“一阴一阳之谓道”开启了多种多样的探究模式。以观念的方式重建形而上学,或许就能围绕着“一阴一阳之谓道”走出一条不一样的形上之路,从而会通“无极而太极”的传···

【曾海军】“生生”:作为一种哲学的开端
“生生之谓易”中以“生生”言变化,不同于存在形态的变化观,后者追求一种认识规律。“道”既不能作为某种超时空的实体而存在,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抽象原理,却能先于一切存在物。“生生”可以通过“道”获得同样的理解,而生生之理作为道理,不同于反映气之运行的规律。“无”不能成为一种开端,“生生”才是传统中不一样的开端方式。

【曾海军】一人与天下:晁错之死的政治哲学解读
不同于商鞅作法自毙,对自己的死感到意外和委屈,晁错早就预料到这种不幸的结局,并准备为自己追求的秩序而死。晁错寄希望于景帝以“一人”的气概承担天下一统的大业,景帝却十分吊诡地以“天下”为由,把他当成“一人”而杀害。景帝与晁错既然站在同一个阵营实施削藩,君臣之间就必须共进退,而决无中途背叛之理,其杀晁错就是现实版的“杀···

【曾海军】“知十”与“道一”:颜、曾传道发微
仅就孔门后学而言,比较多的提法是颜、曾、思、孟,此外就是亲炙弟子中仅以颜、曾并提。自宋儒之后,常以颜、曾为孔门中第一等弟子。颜曾并提大概已是某种共识,本文试图基于《论语》,对颜曾传道在后世获得这种地位,作一点寻根究底的工作。

曾海军 柯 胜 吴 瑶 主编《中华传统文化通识》出版
本书是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曾海军老师领衔主编的一本面向大学生的中华文化通识教材,全书简明而系统地介绍了中华传统文化诸多重要方面,旨在让学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较为全面整体的了解,引领他们深入思考中华文明的本源,感受到它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

【曾海军】汉初政统的延续与更法辨析
贾谊主张“改正朔,易服色”,以兴儒家礼乐的方法更秦之法,但因文帝一方面“本修黄老之言”,另一方面对方术有浓厚兴趣,更容易被阴阳家吸引,故而导致这种更法的失败。公孙臣提出“汉当土德”,几经波折之后才得以取代秦王朝的水德。这意味着儒家的“任德教”更化承秦而来的“任刑法”,最终以儒家的思想品格提升了刘汉王朝在政统上的延续与更···

【曾海军】《论语》伤痛观念的哲学阐明
恻隐之痛乃仁之为体最显豁的开端,乃至于径直地就是仁了。伤痛观念由此获得更为鲜明的哲学品格,其与仁的本体地位息息相关。既要肯定对他人生老病死怀抱的伤痛,同时也要着力加以节制,不能任由其陷溺。

【曾海军】董子哲学的超越之维——以汉初的思想纷争为线索
主父偃只是纵横家,要想获得帝王的青睐,不惜倒行逆施,企图通过“推恩令”在短时间内建立奇功,因此只计较眼前的得失,而董子“大一统”的秩序哲学早已超越一时之功效。公孙弘的功业只能在当下实现,故不惜曲学阿世,极尽所能逢迎汉武帝,董子固然期望得君行道,其哲学理论却能超越一世之功业。经师传承固然功不可没,对于经学的运用却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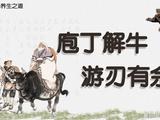
【曾海军】何以“理”解而非“道”解?
庄子一手炮制的“庖丁解牛”已经在思想史上流传了两千多年。庖丁以刀解牛,历代思想者则以思想解庖丁之解牛。

【曾海军】革命与继世:汉初皇权的正当性与稳定性分析
“太子天下本”事关权力更迭的稳定性,儒家通过完备的太子教育将传贤的理想性注入嫡长子世袭制,使得继世的权力更迭方式同样带上了正当性的内涵。“君子大居正”高于一切,而是先前的立子立嫡之法历经让国、尚贤这种儒家大义的激荡与显发,变得更加义蕴丰厚、更加正大光明。

曾海军、李秋莎 主编《古代汉语》出版暨后记
作为中国哲学专业系列教材,《古代汉语》的文选部分按照从今到古的反向顺序排列,以便更好地照顾初学者由易入难的学习过程。与此同时,由今到古的古代文选,又按“人文”“节烈”“为学”“文史”和“经传”等五个单元编排。

【曾海军】繁花似锦的癸卯年会
我没料到自己想为年会写一篇文字,年会一整天的活动结束后,并没起这种念头。外地返回的师友在第二天继续约着聚餐、喝茶和聊天,持续到第三天,吃了一下午的火锅,直到晚上吃完烧烤,我从热闹中抽身离场的刹那间,有一种非常熟悉的离别感油然而生,于是产生了这个念头。

【曾海军】我从新西兰归来
我在新西兰也就呆了两周,而回国后转眼已是小半年了,这个时候再来说“归来”,有点可笑。我其实想用“归来”指某种生活,那种以为不再有这个闲情写点闲话的生活。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停止了这种写作,其中最想写的便是从新西兰探亲回来,几次动手都未能如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