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四新】作为中国哲学关键词的“性”概念的生成及其早期论域的开展
“性”概念是在天命论和宇宙生成论的双重思想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它联系着“天命”和“生命体”的双方。其一,“性”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追问生命体之所以如此及在其自身之本原的问题。它是一在己的、内在的且潜在的本原和质体。其二,“性”来源于“天命”,是“天命”的下落和转化,而人物禀受于己身之中。“天命”与“性”虽有位格的不同,但其实体并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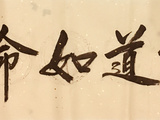
【余东海】孔子可以超越吗? ——东海客厅论儒佛道
孔子可不可以超越?一言以蔽之,其知识境界可以超越,其外王实践境界可以超越,后人理当超越之。但是,其道德境界、即内圣实践无法超越。圣境无止境,不封顶,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但无论怎样高明神圣,不外乎“从心所欲不逾矩”。换言之,圣德圣境是生命最高境界,无法超越。超越圣人,还是圣人。 以为释尊和老子的道德境界超越孔子,那···

【陈晨捷 李琳】“仁”与祖先祭祀:论“仁”字古义及孔子对仁道之创发
在“仁”之意涵的发展与转向进程中,孔子对“仁”作出了新的诠释:一是以“孝”代替“祭”为“教之本”,体现其重现世人伦的精神;二是以“爱人”定义“仁”。

【王正】人能弘道,道亦弘人:孔子的六个面向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至圣先师”“文宣王”,历代有关孔子的著述层出不穷;而经过近代以来对孔子的批判与重估后,孔子现在被理解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之一。这种评价的古今之变,既意味着人们对孔子的理解摆脱了传统中国对孔子的过度神圣化与完美化,又体现着我们现在对孔子的理解其实是在西方的学术分科和现代教育···

倪培民 著《孔子:人能弘道》(修订本)出版
此书是对儒家这一人类历目前影响很广、流传历史很为悠久的伦理和精神传统的深思和启发式的阐述。它具有高度的可读性,并包含了许多有洞察的观点。本书通过大量的历史事例及比较研究的方法,作者力图以通俗和深刻的笔触让读者了解不同角色的孔子: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作为精神的孔子、作为哲学家的孔子、作为政治改革家的孔子、作为教···

【许石林】孔子“携子抱孙”说
2009年9月27日晚,我陪古琴老师王鹏、杜大鹏两位先生一行,从北京连夜开车6个多小时,赶到山东曲阜,参加28日举行的曲阜祭孔大典。在上午的典礼上,两位老师在孔庙大成殿前抚琴——这是不是数十年来首次在曲阜孔庙抚琴,我不知道。下午,我们一行去孔林参观,拜谒历代衍圣公。在第64代衍圣公坟前的祭桌上,我捡了一把饱满的橡树种子,孔···

【卓虞】胡适的宗教经历(对孔子十二分的佩服)
胡适生于一个“僧道无缘”的家庭;爸爸是严守程朱的理学家,对和尚道士非常反感,但在小儿子不到4岁就一命呜呼了。他死后,能撑门面的兄弟又出外做官,家里的娘儿们便无拘无束,拜起菩萨神仙来。小胡适就常常随母亲到庙里求观音保佑,同时也学小朋友用纸匣做孔庙玩,对孔子烧香膜拜,这让他妈妈看了很高兴,希望孔子的神灵能保佑他读书···

【王中江】孔子好《易》和追寻“德义”考论 ——以帛书《易传》中的“子曰”之言为中心
孔子晚年以浓厚的兴趣研习《周易》的事实及其原因,通过帛书《易传》带来的新信息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孔子通过《易》爻辞对德义的追寻表明,其对《周易》的探索主要不在于占筮和预知人生的祝福吉凶,而在于从中追寻天道、道德和仁义等普遍法则和价值。以孤证否众证,以推测代事实,可谓立异,不可谓立新。

【金春峰】论儒学与诗的发展流变
以诗史的几个发展阶段:孔孟荀至两汉、建安风骨、陶潜及唐代杜韩,说明诗的流变——内容和形式与儒学有内在联系。上述诗之特殊面貌的出现,内在原因皆由于儒学之变化。孔子对诗作了自觉反思,肯定抒情诗对生活的重要性,指出生活诗意化的方向。孟荀让诗转向政治化史诗化,导致建安风骨的建立,直接影响盛唐。陶潜田园诗乃生活诗意化的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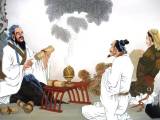
【丁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大意义
“大一统”思想即倡导、推崇和重视国家统一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可以追溯到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孔子“大一统”观念对于中国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境内各兄弟民族在“大一统”的思想基础上逐步凝聚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并进而形成···

【杨朝明】说到读书,他为何偏爱孔子?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这种手不释卷的情愫,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可谓乐在其中。自去年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举办以来,杨朝明委员或就自己熟谙的领域为其他委员释疑解惑,或认真学习聆听其他委员真知灼见。线上线下的交流与交锋,让读书成为委员们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的一种方式。

【张文珍】孔子讲辩证
在人们心目中,孔子似乎是循规蹈矩、严肃的老学究,其实这是一种刻板印象。读读主要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孔子言行的文本,就会发现孔子并不呆板拘泥,相反他在思想与行为方式上很是权变灵活、机智辩证,特别善于审时度势,因地制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合理的选择,体现出鲜明的灵活与变通的特点。

【祝安顺】多面孔子,唯念君子
按照李零先生书中所说,《论语》全书共16022字,含重文(《丧家狗:我读〈论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页),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统计,《论语》中“君子”出现了107次,就全部文字来说,“君子”一词出现频率接近千分之七。如果按照学者所说,“‘君子’与‘仁者’有时可以相通”(吴正南:《“君子”考源》,《武汉教育学院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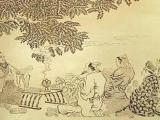
【代玉民】论胡适对孔子易学的逻辑建构 ——从正名方法的角度看
胡适以正名方法进行的逻辑建构并不局限于易学,他进一步将易学推扩到人生与政治领域,使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成为其易学的延伸。最终,孔子哲学成为囊括自然、人生、政治诸领域的广义的易学哲学。

【姚海涛】仁礼合一视域下的孔子生死观
孔子以仁礼合一的理论视域对“死生亦大”这一重大而严肃的人生命题进行了理论观照。一方面,以“生生之谓仁”彰显出对生命尊严与价值的显性评价;另一方面将死亡看做人生有意义的事件,在理论上保留着对死亡的超越,面对死亡时采取了“朝闻夕死”的超然态度。以上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孔子对人的终极人文关怀与理论旨归。

【曾海军】经典、民情与见识——《论语》中的“负面思想”辨析
《论语》中有很多被当作“负面思想”的语录,往往被指出有各种不同的局限性。有见识的学者可以感受经典的力量,懂得其中言情与言理之别,或者能洞悉民情,对“民”的定位既不“失人”亦不“失言”,以及对于《论语》中的思想即“见”即“识”,懂得其超越各种局限性的价值,明白并没有所谓的“负面思想”。

【姚海涛】龙与天道、人道——孔子、荀子对龙文化的拓展
孔子、荀子在龙的具体形象方面并无建树,其主要贡献在龙与天道、人道的理论贯通与文化塑造方面。其对龙文化的新推拓主要体现在龙德与天道方面,具体阐发了龙之德的三个方面,即神圣之德、玄妙之德与君子之德。龙德与人道中蕴含了龙之善恶,以龙喻君子、圣人、君主,龙与人间社会之礼三个层面。

【杨运筹】春秋“王鲁”说刍议:以董仲舒为中心
董仲舒等汉人论定“王鲁说”一方面是上探孔子“缘鲁以言王义”的微旨,另一方面是要处理汉代秦而兴的合法性问题。而在具体处理汉朝代秦而兴的解释学说时,“三统循环”之外尚有“五德终始”,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彼此冲突。出于勾销秦统,为汉立法的意图,董仲舒采用“三统循环”而不取“五德终始”。

【韩星】《论语》仁学体系新诠
孔子思想主体是仁学。“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即仁不仅是人之为人的底线,也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仁”,“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核心、包诸德、合天人、贯内外,通透于其个体生命的成长之中,造就了至圣的人格境界。孔子“仁学”为传统儒学奠定了基本规模和诠释方向,对于今天重建新儒学思想体系具有正本清源、返本···

【余东海】孔子为什么反对铸刑鼎?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业。贵贱不愆,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此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何业之守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乱制,若之何其为法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