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飞龙】《政学私言》中的钱穆法治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钱穆先生是文史大家,在晚年之际口授文章提及“天人合一”,既是最终的文化遗命,也是对秩序法理的终极关怀。法治思考和论述在钱穆先生洋洋大观的诸多著述中并不凸显,主要存留于20世纪40年代的若干篇学术论文之中,以《人治与法治》《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法治新诠》诸篇最具代表性,并均收入《政学私言》之中。这些篇章并非突兀论述,···

【孔庆林】孔子民本思想刍议
自古以来,人们大多认为孔子有民本思想。但具体到一些较小的问题时,会有争议。比如有人认为孔子有愚民思想。如果从孔子的整体精神上加以考察,孔子是以民为本、实行教化的,并不存在愚民思想。认为孔子有愚民思想的证据,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这句话。否认孔子有愚民思想,一是因为断句不同,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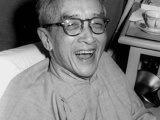
【秦行国】“六经皆史料”?胡适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解释之失
1922年,胡适撰成《章实斋先生年谱》,梁启超对此书评价颇高,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言“胡适之之《实斋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吾尚嫌其未尽,并及时代思潮,凡此诸作,皆近代学术界一盛饰也”。梁氏如此溢美,可见《章实斋先生年谱》在当时声誉甚隆。在《章实斋先生年谱》中,胡适对清代学者章学诚所提的“六经皆史”之论···

【杨国荣】叶适的实学观
作为儒学的一脉,永嘉学派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其展开的脉络和系统。与宋代主流的理学相对,永嘉学派趋向于以“实”拒“虚”。这里的“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即从外部对象出发,而不仅仅根据人的主观想法和意念去行动;其二,注重事功之学和经世致用。与之相联系,永嘉学派主张“事上理会”,扬弃“无验于事者”。

【孙廷林】杨起元心学思想的岭南学术渊源
杨起元(1547—1599),字贞复,号复所,广东归善县(今属广东惠州)人,泰州学派罗汝芳高弟,是晚明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杨起元心学思想继承了泰州学派的思想观点,坚守良知是心的本体,并深受白沙学影响,讲究“致虚立本”的认识论。杨起元心学思想主要与两方面的岭南学术渊源有关,具有浓厚的岭南学术色彩。

【陈卫平】孟子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治国层面,孟子的仁政蓝图有着涵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丰富资源。孟子的仁政以“制民之产”即解决民生为基础,直接涉及到富强的问题,提出以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富民的起点。在社会层面,“义”和“礼”也存在着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资源。义作为社会应当如此的价值准则,包含着对自由、公正的思考。义作为人们行为···

【尔雅台】全球性的孔教与文化软实力战略
民间孔教事业,起于儒家教化既衰之后,任重道远,事繁必艰,故必须通过"孔教会"以组织化制度化社会化的力量来承担。由是,正如蒋庆指出的,中国将再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文明属性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一味模仿西方的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且自我撕裂"的现代民族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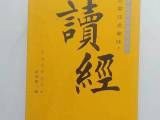
【胡晓明】最大的吉祥是文明的吉祥
儒家经典的背后,温柔敦厚、知书达理、和平理性、社会和谐、乐善好施、刚健积极、注重人道人生人性的儒家文明观,这样的文化所熏陶的人,可能是中国人未来十年走向世界而更受欢迎的形象。

【方旭东】“远者来”:关于外来移民问题的儒家智慧
移民是重要的人口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中国的国际移民也日益增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来移民的接受显得十分保守。无论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这个局面都亟待突破,而首先需要解决的则是对外来移民的认识问题。古典儒家处理外来移民的智慧值得借鉴···

【姚中秋】经史传统抑或文史哲传统
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中国研究方法是经史之学。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是传统经史体制崩解后,被迫寄身于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残片。如果我们意欲接续中国学术传统并予以弘大,那就应当接续经史之学传统,尤其是发现并弘大20世纪的经史之学,从而在更大范围的新天下发展中国式社会科学体系。

【李晨阳】疫情与伦理价值——兼评范瑞平教授的〈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
在我看来,自发的协调性(即没有统一操控的协作)要比具有神秘色彩的荣格的共时性更能说明儒家的和谐概念。同时,我不排除因果联系在和谐过程中的作用。我尤其赞成范教授关于“和谐主义是儒家伦理学的首要特点”之观点。

【白彤东】描述还是规范,政治还是伦理?——大疫当前的思考
我认为,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契约传统,而是超越国家的全球化是由为了自己利益可以不顾一切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主导这一悖论。对此,我也在我的新着里提出了以“仁责高于主权”为原则的儒家新天下体系。我想,上述在政治与制度层面上的努力,也许才是大疫当前,儒家能够做出的贡献。

【方旭东】“五伦”并不排斥契约——读范瑞平教授〈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
范教授强调儒家不以契约关系理解家人关系乃至五伦,可能是出于对契约的某种成见,这种成见以为,凡说到“契约”,就是西方功利主义所讲的那种带有很强的物质利益交换意图的契约。儒家固然没有这种强烈的功利意图,但也并非毫无平等互利的契约意识。

【王占宇 梁飞】从福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看儒家伦理学的世界前景
福山对儒家文化的当代愿景多有论述。分析福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是观察大疫背景下,儒家伦理学在西方伦理学界处境的有益管道。

【张言亮】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是否能够更好地解决当前的疫情——读范瑞平教授〈大疫···
范瑞平教授重点阐述了“为什么应该主动诉诸儒家文化的伦理资源来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危机以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究竟是什么?儒家文化的伦理资源如何解决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危机和挑战?

【王珏】儒家和谐文化与新冠疫情应对
笔者非常认同范教授的此一主张,也基本赞同他所提到的儒家和谐理念应对新冠疫情的殊胜之处。但正因为这一主张在思想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它值得细致的审查、辩护和批判。本评论试图从儒家和谐文化的角度回应新冠疫情应对中的关键问题,也是与范教授进一步商榷。

【李瑞全】敬评范瑞平教授大作《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兼论儒家义···
儒家自然反对如此坐等病毒肆虐的「佛系模式」,西方社会最后也都全力去防堵病毒,没有任由病毒肆虐到尽的方式。西方也有年青人认为自己身体强壮,不怕病毒,或认为这只是一种流行感冒之类,因而轻忽不理,以政治之自由权利来拒绝政府强制戴口罩,禁止聚会等限制令。此与西方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无关,更与原则主义无关。但由此而产生对···

【范瑞平】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
东亚国家对于这次疫情的应对,至少在疫情明显出现之后,总体上处理得较之西方国家更好,背后实有不同的伦理精神的反应和支撑。本文诉诸儒家美德伦理学的资源,宣导人类进行伦理学的范式转向:我们需要和谐主义(而不是科学主义)的发展观、美德主义(而不是原则主义)的决策观、家庭主义(而不是契约主义)的天下观。

【王庆新】儒家伦理与现代西方伦理的异同:回应范瑞平教授
中国在这次疫情应对中取得可喜可贺的成绩,而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至今仍是疫情重灾区。福山认为中国的强大执政能力是关键因素,但是正如范文所指出的,儒家传统伦理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可是却被很多人忽视了。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儒家伦理的重要性,需要重新认识儒家伦理学相对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优越性,需要思考为何大疫当前儒家伦···

【周景耀】理学家诗的消失——以钱锺书的论述为中心
钱锺书对理学家诗的批评体现了其思想“趋时”的双重性:表层的与意识形态相呼应的“趋时”和深层的与二十世纪以来借助西方思想“重估”中国传统的潮流相激荡的“趋时”。前者表现为在《宋诗选注》中理学家诗的大规模缺席,后者表现为他以理念说、审美无功利说等西方现代美学观念为理论资源“重估”理学家诗与中国诗学传统,对诗的认识亦藉此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