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佳明】刍议“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与岳麓书院
刍议“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与岳麓书院,这个题目看起来有点散,其实有一条线索,把这三样东西连接起来、贯穿起来。这条线索就是“认识论”。湖湘文化也好,湘学也好,跟认识论有很大关系。

【杨永涛】“自爱”:先秦儒家的成人之道
儒家的学问究其根本是做人的学问。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去达成这样的目标?是孔子以降的儒家学者所共同追寻的目标。而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需要从先秦儒家,也就是儒学的原点处出发,将相关概念梳理清楚。

【聂菲璘】我国历史上的选贤制度
“选贤与能”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与”通“举”,“选贤与能”亦作“选贤举能”,即选举贤能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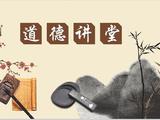
【刘余莉】强化道德教育对法治的支撑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大学》开篇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论语》中记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国古圣先贤在体悟“道”的基础上,把人的“德”统之于“仁”,并具体在社会立身处世、齐家治国时所体现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也称为“八德”。正是这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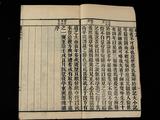
【宋玲】“大同”理想的文化解读
《礼记·礼运》中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大同”,代表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最高憧憬,表达了一种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追求。此一憧憬和追求,历数千年,始终是中华传统思想的主流,具有重要的价值。

【虞万里】经学学者撰写的经部善本书志
所谓学者,就是一个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形成思想解决问题的人。书有未曾经我读,于是就尽量找到书的提要或书志类书来充实知识。

【张怀通】“尚书”源于礼仪说
“尚书”即上古之书,是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献及其汇编。今天所见文题俱在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的《康诰》等28篇、今本《逸周书》的《世俘》等59篇,以及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摄命》等十多篇。这些“尚书”中可信度较高的篇章,如《康诰》《世俘》《祭公》等,其形成多源于当时的献俘礼、封建礼和养老礼等礼仪。

【马克·安德鲁西奥】新冠时代黎明的阴阳、佛陀、和柏拉图的洞穴
新冠疫情时代的黎明,量子般跳跃进入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全球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其发展前景已经赶超几十亿人的设想。

【西尔翰·莱昂斯】我们渴望自由吗?
西尔翰·莱昂斯(Siobhan Lyons)发现自由意志的到来并非没有代价的。

【莫顿·霍伊·杰森】没有上帝也没有理性
阿尔贝·加缪清晰地面对人生的条件。

【琳恩·小笠原】即将淹没的世界中的等级体系 ——贝淡宁、汪沛著《正义层秩论》简评
过去一些年,贝淡宁的著作受到不少批评,有人暗示他是在为中国的政党国家辩护,不过我觉得这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他的观点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有关传统东亚思想中发现的社群主义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如何指导了政治体制和生活生活---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在西方,人们往往瞧不起官僚机构,非专家组成的政府和无情的商人心···

【安德鲁·多伊尔】别害怕面目狰狞的收割者
我们已经不愿意承认死亡是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新冠病毒疫情或许给我们更加切合实际的死亡态度。

【吴钩】冬天来了,宋朝是如何救助流浪乞丐的
如果你展开《清明上河图》,仔细些看,可以在画中的城门外,找到三个乞丐,一个似乎是残疾人,坐在地上乞讨,另一个是孩童,还有一个是位老妇人。可谓很有代表性。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急剧,贫富分化悬殊,城市里出现大量流浪乞丐,是不必意外的事情。

【胡大雷】“立言不朽”与“以文报德”
《左传》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其中尤以“立言不朽”对后世影响为大,并有一些衍生意义,涉及“立言”的目的、传播、功效等,以下作一点探讨。

【王齐洲】《乐经》是文字典籍而非曲谱辨
《乐经》是儒家经典中最尴尬的一部经典。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独《乐经》未立。王莽立《乐经》博士,后人指其伪造,两千年来,聚讼不断。至于西汉末年王莽奏立《乐经》博士,其《乐经》究竟是古文经还是今文经,这需要放在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大势中去理解。总体上说,汉哀帝之前,朝廷所立经学博士皆今文经博士;平帝以后,朝廷所立···

【李竞恒】 江浙两头婚的历史渊源与“存亡继绝”
江浙地区民间正在自发兴起一种“两头婚”,即男不娶女不嫁的小家庭,兼顾男、女父母双方家庭,生两个小孩,分别跟祖父、外公姓。对于江浙地区两头婚的兼顾父系、外祖系这一现象,在独生子女特殊时代,尤其具有“存亡继绝”的仁义意义。并且,也符合传统华夏习惯法的补充救济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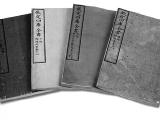
【耿海军 刘瑞一】中华典籍怎样才能更接地气 ——“四库学和易学的当代价值与传播”···
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与中国屈原学会四库文化研究分会联合主办的“四库学和易学的当代价值与传播”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据会议组织人员介绍,“四库学”“易学”每年分别组织研讨,“四库学”之前已经组织3届,而“易学”已组织10届。今年,考虑到疫情,将两个会议合并为一个。

【宋立林】丰腴的面孔——《孔子家语》中的孔子
本文从“谈天”“为政”“重礼”三个维度,择要指出《家语》对于理解孔子的重要价值。

【宋立林】先秦时期“小康梦”的萌生与丰富
大同之“大”,与“小康”之“小”,两个形容词,早已明白宣告了二者之间的层次差异。如果说,大同是最高理想,小康则是现实目标。中国思想家们,既擘画了大同的终极理想,给人们勾勒了一幅“理想国”的圆满图景,也不忘规划小康的现实目标,描绘可望可及的美好生活。

【廖晓炜】康德还是海德格? ——读盛珂新着《道德与存在:心学传统的存在论阐释》
牟宗三哲学长期以来都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在此背景下,要在牟宗三哲学研究方面谈出新意,似乎是件十分不易的事情。然而,盛珂教授新着《道德与存在:心学传统的存在论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却为我们重新审视牟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