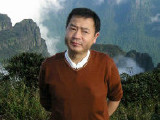
【余东海】追求黄金事业,开启黄金时代 ——东海客厅论时局
处于左右的夹缝,儒家会很艰难,但无大虞,只要自家争气,也是成长和发展的大好机会。儒家劫后方归,整体上思想修养、道德修养和政治能力都很有限,如果一帆风顺信者盈谷,非儒家之福、中国之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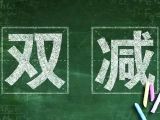
【曾海军】“双减”之后话教养——有感于一则反咬补课老师的新闻
对于国家的“双减”政策,作为身在教育行业中的人,并不难明白,虽然会有很多阵痛,但从长远来讲,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没有特别的关注,只是无意中看到一则新闻,令我突然有了些想法。新闻中说,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有一对双胞胎的家长,通过中间人花钱找一个物理老师补课。补完课后便反咬一口,举报物理老师违规补课,不仅要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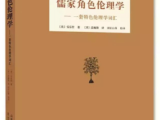
【安乐哲】“成人、成仁”之内在性
我们已经看到,在儒家这个我称为“human-becoming”(“成人”)的模式里,人的个人实现是不可还原(简约)地“包含他者”(“other-entailing”)而且一切关系皆是含有亲属性的。朋友也变成家庭成员。个人幸福、家庭兴旺、国家繁荣都是同构和不分的。我们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的“human being”(“人本体”)概念,这样能把“human being”和“human ···

【贾登荣】解读儒家经典的文化密码——刘强著《四书通讲》读后
所谓《四书》,是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四部儒家经典。一般认为,它们出自于先秦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故又被称作“四子书”“四圣书”。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强,“坚信中华传统文化之道对于今日世界和人类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数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跋涉于中国儒家经典的瀚海之中,逐渐“勘探···

【余东海】内圣何以开外王 ——东海客厅论圣王
内圣外王说出自庄子,虽为历代儒家所用,只能是方便说。严格地讲,内圣非内,外王非外,道德对政治具有覆盖性和统摄性。儒家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统摄人道之一切,当然包括政治。仁义道德之外焉有政治,圣贤君子之外焉有王道。

【许石林】趾高气昂地践踏礼俗传统,高举“现代性”才是不折不扣的迷信
轻易地把生产和销售纸人、纸马、纸房、冥币等定义为“封建迷信”,是草率的,没有认识到中华传统风俗礼仪尤其是丧葬祭祀的深义和作用。那种动不动就追根溯源,如考察纸币所产生的历史以证明烧纸钱并非中华古礼固有之俗等等,而不是从义理上体察领会其中精神价值的,貌似科学求实证,实则最迂远不经。

【方朝晖】良心、底线与当代伦理——读何怀宏《良心论》
何怀宏的《良心论》一书摆脱了传统心性儒学孤、高、深的路数,在借鉴儒学资源的基础上,试图开辟一条基于所有人而不是少数精英(或精英群体)的伦理重建之路。它以"底线伦理学"为特色,关心每一个现代公民都应履行的基本道德义务。它以良心/恻隐之心为道德动力之源,试图开辟一条人人切实可行的道德建设途径。本书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

【顾春】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和巩固
在西周,周天子通过分封制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又通过宗族长来统治各自宗族的人民。其中,分封对象体现的是尊,宗族治理体现的是亲。就这样,周朝最高统治者按照亲亲尊尊的原则、通过制礼作乐,建立起统治秩序。
.jpeg!cover_160_120)
【张永路】中唐《春秋》新学开启宋代新经学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纷乱之后,隋唐时期又迎来了统一的时代。从学术发展史来看,《五经正义》的编订成为这一统一时代的经学表征。《五经正义》是魏晋南北朝义疏经学的集中展示,是过去数百年经学发展的集成汇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集大成往往也意味着类型的终结。中唐时期之后,学术思潮的创新因子逐渐显现。韩愈、···

【郭丹】先秦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格局
方铭教授的专业主要是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但其新著《方铭孔子暨儒学文化研究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却避开了纯文学研究的路径,有意选择中国传统文化源头所自的核心内容,从经学、诸子、辞赋研究中选择部分与孔子和儒学相关或有助于认识孔子及其影响力的文章集结成书,目的在于展示先秦文学所产生的宏厚渊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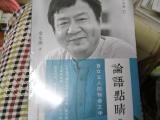
【余东海】可以治一国,不能平天下 ——自由主义的优缺点
自由主义优点多多,远远优于极权主义恶制暴政和神本主义的政教合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总结世界饥荒史时说了一个结论:“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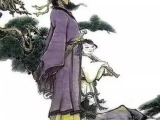
【李林杰】以文济野:中国儒学之复兴
中国儒学内涵的“向文性”,构成了当今世界济“物欲横流”之穷的必然所向,而其“诠释学传统”特色下的文本模糊与跳跃逻辑,构成了儒学现代性转化之可能性所在。但尽管如此,我们需要的更多是“平视之自信”,而非“俯视之自傲”。
-18.jpg!cover_160_120)
【吴钩】“包青天”告诉了我们多少假的历史?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这首歌说的是北宋开封府知府包拯。哦,不对,是包公戏里的“包青天”。这“包青天”可跟历史上的包拯毫无关系,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主要内容便是说,从元朝开始的所有包公戏,除了包拯的名字是真的之外,其他的全都是假的,包括包拯的相貌、经历、审案故事、司法程···

【成富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辨正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观点,被公认为传统史学之极则。钱穆称之为“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但史公三句中“究天人之际”一语的确指究竟何在并不明确。对此,钱先生认为:“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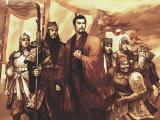
【林存光 陈林】政由谁出 政治何为 ——孔子政治哲学新论
政由谁出与政治何为是政治哲学的两大核心议题,孔子对其作出深刻思考并给出了明确回答。孔子的私学教育致力于培养具有完美道德品格的士人君子,而在他的新政治构想中,士人君子是治国为政的理想主体,其资格的正当性就来自君子所具备的人格特征与精神品格。孔子基于人类"性相近,习相远"的复杂特性提出"学以致其道",在不破坏人类习性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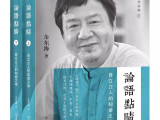
【余东海】邪恶势力的特征和宿命 ——东海客厅论因果
所有邪恶势力都有以下共性:冷酷无情,贪婪无度,卑鄙无耻,暴虐无忌,反复无常,以怨报德。以怨报德即忘恩负义和恩将仇报。有人指出一个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当年大力帮助支持m乃至救过它命的人大多结局很惨。
-34.jpg!cover_160_120)
【许石林】还迷信补课?农村识字不全妈妈手抄唐诗三百首,将两个儿子培养成国学才俊
刘氏昆仲,九零后生人,出身河南项城农村,父母务农打工,识字不多但皆仰慕文化。刘父外出打工,每返乡,必携带从各地拣拾之旧书杂志回家。刘母仅小学四年级学历,曾见本家长兄家中有《唐诗三百首》,虽不尽识读,但用记账白纸本,仔细照描照画,把整本《唐诗三百首》照样抄描一遍,教二子念诵。

【吴钩】金庸告诉了我们多少假的历史?
金庸写武侠小说,除了少数作品有意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模糊处理之外(如《笑傲江湖》),绝大部分的作品都交待了明晰的历史背景,将虚构的传奇巧妙地揉合进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其中以宋代为故事背景的有四部:《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与《倚天屠龙记》(“倚天”的主体故事虽然发生在元末,但小说开篇是从南宋末年切···

【张凯】文明的估价与开新: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
近代中国儒学面对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流变展现出“和会与辩驳”的齐头并进,各派学说因时而兴起,依据各自传统、立场与义理关怀。融汇中西,沟通新旧诚为学界共识与学术大势,然“学术之事,能立然后能行,有我而后有同,否则不立何行,无我何同”。确立文明主体性及其价值是中西之间“和会而融通”、“兼举而并包”的前提与基础,“苟有···

【杜华伟】《养德经邦:当代书院学人访谈录》后记
今天出版社发来封面设计初稿,经过一番纠结后确定了印有话筒的一款,因为感觉话筒挺契合“访谈”这一主题。随意跟兰州凤鸣书院严荣华院长分享此消息,没想到她当即决定预购400本作为书院三周年庆的伴手礼。我很真诚地说著作出版后会送她几本,但作为书院周年庆礼物似乎有点高调。她也真诚地回复我“书以载道,载的这个道需要传播。您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