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飞龙】中英联合声明不是外国干预香港的合法性基础
联合声明是一份有效、重要且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律文件,但它绝不为任何外国势力建构任何超越1997年时间框架的管治权和监督权。香港基本法不仅完全吸收了联合声明中的中方单方面声明,而且基于中国主权意志而增加了普选条款,提升了香港民主权利。

【吴钩】重新发现风雅宋朝 ——“吴钩说宋”系列的创作手记
自2005年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一本《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之后,我关注的重心一直是宋代史,以“重新发现宋朝”自勉,并于2018年与2019年先后出版了《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两本书,构成“吴钩说宋”系列。研究宋代史的方家很多,他们的学术论著是我的案头书,我能做的,只是在前辈们的研究成果···

【余东海】东海态度(十一)
骂贼赞圣,君子本分。对盗贼不反对不批判,对圣人不崇拜不赞美,非君子也。圣贼之间,尚有贤者、君子、士人、庸人、小人各色人等,对他们的评判都应如理如实,实事求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苟誉苟毁乡愿乡讪,非君子也。

明报社评:师生情绪要关注,港中学罢课不可取
罢课作为一种表达政治诉求的手段,无可避免会影响学生正常学习,恰当与否要视乎很多因素,不能简单说“成年人有罢工自由,所以学生也有罢课自由”,将一切罢课行动合理化。

【余东海】东海态度(九)
缘来不拒,缘去不留,有缘惜缘,无缘不攀,一切随缘,无可无不可。刻意绝缘和刻意攀缘,都非人生常态。攀附权贵固然是攀缘,好为人师也是一种攀缘。故孟子强调: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佛教提醒:佛不度无缘之人。
.jpg!cover_160_120)
【田飞龙】提名“绿化”与台湾司法的政治化
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以来,从其根本性的台独党纲出发,在两岸关系上否认“九二共识”,寻求“离岸替代”,实行极端的转型正义和去中国化政策,在岛内治理上则一方面政治封杀国民党,另一方面则滥用执政权全力准备“台独”相关条件。

【罗伯特·纽曼】孤寂世的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如何帮助恢复公共利益的核心地位?这是走向集体行动的基本步骤,而集体行动是解决当前的宪政和生态危机必不可少的东西。

【余东海】东海态度(七)
欲向我学儒,欲与我交往或争鸣,欲对我进行批判,欲为儒家取精去糟,都应该对儒家思想有所了解,也欢迎对我的文化、政治和人生态度有所了解。兹将有关“态度”的部分微言汇集于下,聊作自我简介,供有志之士参考。

【刘海波】不要让香港成为东亚孤儿!
原有的基本法框架有问题,主要在于中央没有落地执法权和司法终审权,这也是迟迟不能在香港推行真正双普选的原因。
-90.jpg!cover_160_120)
【吴笑非】文化復興的邏輯及實例
中醫和漢服的復興,是有啟發意義的文化事件。我們不應僅停留在現象的認識,而應該深入思考其背後的社會發展規律,並升華為理論,服務於我國軟實力的塑造。

【余东海】东海态度(六)
或谓东海孤寂。孤独感或有,寂寞感毫无。思考创作独饮独乐,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唯感觉时间不够花,哪有余闲和兴趣与外人打交道哉。不要打扰我就是对我最好的尊重。为了节省时间,我忍痛割弃了多种爱好,比如拳技、气功、诗词等等,也尽量节制朋友交往和山水游玩。

【吴钩】“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所谓真相是怎么来的?
我曾以《水浒传》里的潘金莲与西门庆故事为引子,写了几篇介绍宋代司法制度的小文章。结果不少网友在文章下面留言:“小编,真实历史不是这样的哦,历史上武大郎和潘金莲很恩爱,并且武大郎不是做烧饼的。”“小编,请多看历史、少读小说。”“稍微看过历史的就不应该这么写武大郎和潘金莲,武大是县令,潘是大家闺秀好不?傻逼小编。”看得···

【房伟】精神信仰与文化传承——对文庙从祀的思考
孔庙大成殿的东、西两侧,有两排房屋,绿瓦长廊,红柱隔扇,习惯上称为“两庑”。走进两庑,一个个木制的牌位整齐地摆在神龛之中,神龛前的方桌上摆放着祭祀用的礼器。

【沈洁】晚清时潮中的顾炎武:援引、印刷及历史语境
晚清士林的顾著阅读,既有曾国藩、章太炎这样的大儒,为经国大业、学术传承、道德接续;亦有汲汲为功名计、为稻粮谋的芸芸读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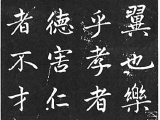
【王利民、江梅玲】关学语境中的张载诗
北宋时期,与濂学、洛学鼎足而立的是关学。随着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丝绸之路”被阻断,对外交通由陆路转向海路,北宋时期的关中不再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黄震云】礼乐:春秋时期治理国家的有效方式
现存十五《国风》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早期中国的礼乐制度和政治文化传统。先贤以礼乐作为治理国家最理想、最有效的方式,古代君王往往将礼乐赏赐给有功德的诸侯,这成为风诗最主要的合法来源。随着礼崩乐坏,周王室音律标准被抛弃。最终,经过孔子删订,《诗经》成型,被奉为儒家经典。

【余东海】东海态度(五)
欲向我学儒,欲与我交往或争鸣,欲对我进行批判,欲为儒家取精去糟,都应该对儒家思想有所了解,也欢迎对我的文化、政治和人生态度有所了解。兹将有关“态度”的部分微言汇集于下,聊作自我简介,供有志之士参考。
-1.jpg!cover_160_120)
【寇丹】人性良知与文化根脉
现在报刊或电视诸如《乡土》、《记住乡愁》,包括味道乡情一类的节目多了起来。不过总觉得在多姿多彩和新奇的表象之余,少了点中华各民族、地域都该有的一条根。

【赵天】孔与佛之间的抉择: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
梁启超一生的宗教选择和对于宗教的态度则可以给当今的孔教主义者们以启发,即我们是否有必要将更多的目光注视于政治与国家这些问题。毕竟这些问题对于普通的生命来说过于高远和宏大。
-2.jpg!cover_160_120)
【田飞龙】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需要法治的支撑
我们知道,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当中有个说法,叫做“纽伦港”,就是纽约、伦敦、香港,大家打开24小时的全球时区,这三个地方正好是三分天下,它们是全球金融市场秩序的时空和秩序连续性的关键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