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军】汪绂:一意精进 终至大成
清婺源人汪绂(1692年—1759年),《清史稿》称其“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畅”,尤以宋代五子(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之学为依归,著作等身,被后世学人广泛认可,尊之为大儒、通儒和醇儒。

【蔡相龙】司马光的“诚信之道”
北宋大儒司马光,字君实,人如其字,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司马光自我评价:“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其胸襟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无论是为官、治学还是处世,始终秉持诚信之道。
-2.jpg!cover_160_120)
【谈火生】治体论与政体论是对立的吗?——任锋新著《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读感
中西方都有“治体论”,但各有特色。我不赞成将“治体论”作为“政体论”的对立物,它们之间不应该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相参照的关系,它们完全可以在相互观照的过程中丰富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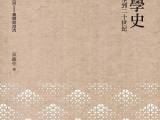
【衷鑫恣】以妓女羞名儒:从明清小说家到五四文人的反儒套路
自古以来,名儒与妓女(艳女)的故事是文学与民间热衷的话题。

【余东海】暴君和革命
桀纣和嬴政都是著名暴君,但性质大不同。桀纣之暴是个体性的,没有相应的极权文化背景和制度基础。君王之暴固然会败坏礼制,却也受到制度一定程度的制约和各级官员不同程度的抵制。嬴政之暴则是道德性、文化性和制度性的统一,由邪说恶制暴君组合而成的极权暴政,罪恶全方位,灾害无止境。

【李明辉】如何继承牟宗三先生的思想遗产?
牟先生就像古往今来的大哲学家一样,留下一大笔思想遗产,唯善学者能受其惠。善学者既能入乎其内,亦能出乎其外,但此非易事。能入乎其内,而未能出乎其外者,犹有所得,胜于在门外徘徊张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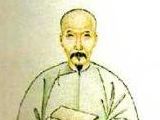
【李圣华】清代朴学中的“浙派”
清代浙学在经学、史学、小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近三百年清代学术发展演变深具影响。

【彭国翔】挣扎与孤寂:牟宗三的爱情世界
牟宗三以哲学家名世,但他并不只有冷静的理智而“太上忘情”。只要阅读牟宗三的相关文字,就足以感受到其人情感之强烈与真挚。

【李细成】康有为谭嗣同弘扬儒家入世精神的两个维度
为了应对基督教的理论挑战,康有为刷新了传统儒学入世天游的修道空间,谭嗣同则激活了传统儒学入世永生的成道时间,他们知行合一地光显了传统儒学入世立功的弘道时空。

【余东海】做一个纯粹的好人
元士少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做人,要么好的纯粹,要么坏的彻底!”东海少时也以一句略同的话自许:“比君子更君子,比小人更小人。”此话还被一位老作家写进了为我诗集所写的序言里。

【田飞龙】当务之急,恢复香港法治和发展基础
香港反修例运动绵延数月,从和平示威一步步发展为极限施压式的暴力冲击,已经公然挑战宪法和基本法权威、中央政府权威、国家主权安全,严重损害了香港非常珍贵的法治精神,损害了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和根本利益,也严重伤害了包括700多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感情。当持续的暴力因素累加到一定程度时,香港的法治与民意的归位就···

【蒋芳】读经少年归来
十多年前,“读经运动”进入高潮,国内涌现了近百家读经学堂,大批少年从传统教育体制中跳出来,进入读经学堂求学。然而,读经到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毒害孩子?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争论不休。

【齐义虎】优化一国两制,亟需修法补洞
中国虽然承诺香港高度自治的大原则五十年不变,但不等于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不能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调适修补。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只有夯实一国的基础,才会让两制健康成长。为了香港能更好地自治,中央应该拿出政治勇气和政治决断力,实事求是地检讨《基本法》的制度漏洞,担负起中央政府的宪制责任,由全国人大进行修订。

【许石林】国花,永远评不出结果才好呢!
世上没有不好看的花。即使生得再丑陋的植物,其开出的花都很美,甚至,有些植物越是难看的身子,开出的花越美。

【余东海】儒家文化特区构想
儒家文化特区,特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的特区,文化、制度、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无不儒化,无不具有中华特色。

【刘海波】完善香港、澳门《基本法》人大释法机制的建议
香港、澳门《基本法》“特别行政区法院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这一机制的运转并不畅通。一国两制的复杂性、基本法的框架性、香港法治的特点,联邦制普通法国家司法权的安排,都说明完善此人大释法机制对“一国两制”的成功极为关键。

【知一】自由主义宗教观的严重缺陷
及时反思自由主义宗教观之法律-公民-多元宗教架构的问题,在高压反分裂同时,察其根源,重归近悦远来之道,“少数民族”之所以为“少数民族”在于其人数上为少数,奉行其习俗、价值之人数为少数,汉族作为主体性民族,不在血缘为汉族,在奉行之习俗、伦常、价值为一稳定、良善、美好之习俗、伦常、价值,其根源在儒家教化。内陆省份皆社泰···

【田飞龙】“反修例”升级动摇香港核心价值
事实上,陈云与戴耀廷本身都可能未必充分估计到其理论误用和滥用的严重政治后果。不过,任何理论之风行,也绝无可能仅仅是理论家的咒语功夫,而是与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精神困境有关。
-12.jpg!cover_160_120)
【王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是你想象的吃货生成记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王蔚先生,从孔子“不撤姜食,不多食”说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当然这不是你想象的吃货生成记。而是一篇从孔子吃姜到中庸的精彩之作。我也爱吃姜,不是因为孔子,不是因为王蔚教授,而是真心喜欢。你也爱吃姜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此妙文。
-27.jpg!cover_160_120)
【许石林】张扣扣案,你凭什么说尘埃落定?你考虑过尘埃的感受吗?
是的,本来我的老家能干一件多么漂亮的事儿,我着急,就跟盼着老家的球队能进球一样,可是,谁知道他们非常正确地踢偏了。


